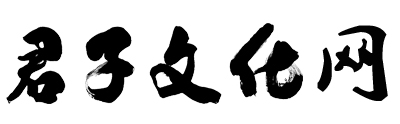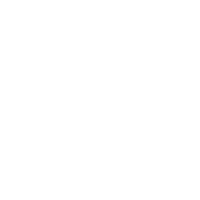人本敬畏与神本敬畏
——兼论儒教与基督教的道德心态
李向平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张建民 博士
内容提要: 敬畏作为宗教知识系统的核心问题之一,可由敬畏关系而衍生出特定宗教的道德心态。儒教是一种人本敬畏,基督教则基于神本敬畏。比较而言,儒教的人本敬畏以天命、 大人和圣人之言三大敬畏为主要框架,构成性善论的信念预设、成圣希贤的价值目标、 修身涵养之道德行动而形成强调“诚”的道德心态;而基督教的神本敬畏则以上帝或 唯一至上神的敬畏为法则,并以性恶论的信念预设、因信称义之价值目标、遵守律法 之行动形成强调“信”的道德心态。通过儒教与基督教两种敬畏框架及其道德心态比 较,可以更深入而具体地理解儒家道德心态的主要特征,为其现代转型和创造性发展 提供文明互鉴。
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视域,世界文明史中的宗教类型大抵能够被理解为“人本信仰” 和“神本信仰”两大类型 A ,并且在各自的文化实践中衍生为“人本敬畏”和“神本敬畏”, 进而深层作用于道德价值的生成、运作等心态和秩序之中。其转化生成的基本价值观念从历 史一直延伸到当下,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心态变化。因此,敬畏可以作为 不同文化之间道德价值比较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以敬畏作为理论工具来探索中国三千年来文 明和文化所积淀的道德心态,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道德心态进行比较,以实现文明互鉴之 目的。
一、敬畏作为道德心态的核心构成
道德价值目标在儒家是“圣人”,在基督教则是“义人”,它们分别代表着儒家传统和基 督教传统的不同神圣原则 , 为此而形成两种不同的价值信念体系,是人之生命得以开展而“所 依靠之一切” B 。“圣人”和“义人”的价值信念目标都离不开两种文化中的敬畏形态,无法离开终极道德价值目标的设定,以及用理想人格构建自身的道德生活样式。它们不仅可以作 为神圣根源和道德法则的特点,还能直接以心态结构的形式制约着一个文明演进的机制、速 度、广度和深度,形构了人们对文明发展的反应和理解,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知识观点、 行动框架,心性的态势,呈现出敬畏与道德心态的内在关联。
一般而言, 敬畏可分别以“敬”和“畏”进行理解。“畏”固然是一种害怕或惧怕,但却 不是一般的惧怕,而是在宗教意义上的神秘之畏,对神圣者或神秘者的恐惧。相对于“敬”,“畏”更具有本源性,从宗教演变来看存在着“由畏生敬”的历史过程。 A 因此无论是儒家 还是基督教,其信念体系中的“神圣”之产生都有一个从令人回避的神秘畏惧到令人着迷的 神圣向往之转化过程 B 。这反映了文明早期人类共同的存在状况:面对未知力量时的害怕和无力。
在中国文明中,“畏”字来源于“鬼”字 C 。“鬼”者,“归”也,人死之后,无所归属便 成为令人畏惧的“鬼”。故在殷商时代人们畏惧鬼神的同时也重视鬼神之事,所谓殷人“先鬼 而后礼”D 。随着殷周之际发生巨变,承载“敬”的“礼”的地位得到彰显,祭祀礼仪将敬畏 整合为一处,这便是儒家主张的“祭思敬” E 。“祭思敬”的要旨是通过祭祀之礼将神秘的畏 惧转化为“敬”,以“敬”内涵“畏”,人和神便可共存,人神的秩序得到稳定。由此形成中 国人敬事天地、尊先祖、重祭祀的礼乐文明,进而表现为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总是与天、祖等 敬畏对象紧密关联。
反观基督教文明,其来源于希伯来文明中的犹太教。敬畏一词本用来表示人对神无可言 状的巨大恐惧感。因为人的罪和在神面前的无价值,所以人必须由神的恩典而得救。在犹太 教更强调人对神之律法的持守,而基督教则强调因信而得救,使民族性宗教拓展成普遍化宗 教。由于神乃敬畏之源,故基督教之道德心态由神而获得规定性。
因此,敬畏最初乃是一种神圣性、其后则带有宗教性的情感,其不仅是神人关系得以存 在和稳定的“粘合剂”,也是文明形态形成的纽带。重要的是, 敬畏能产生伦理命令,促使人 展开一种道德生活,故可视为道德心态的根源和核心构成。以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来看,儒 教和基督教的基本差别之一可谓是人本主义信仰或者神本主义信仰的差异,并且在中西方历 史过程中衍化为强调道德修养和强调宗教信仰的不同,最后导致中西方社会特点的不同。
二、人本敬畏和神本敬畏
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价值信念体系属于人本主义信仰,唯一至上神为核心的基督教 文明价值信念体系属于神本主义信仰。人本主义信仰是以超社会力量崇拜为核心的信仰,而 神本主义信仰则是以超自然关系为基础的信仰,二者都是一种信仰、敬畏神圣的观念结构与 行动体系 F 。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两种价值信念体系各有长短,在敬畏上表现为人本敬畏和神 本敬畏两种类型。
人本敬畏在儒家传统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G 。在这种敬畏结 构中,“天命”是根本性的敬畏 H ,可分殊为“天命之所存”的“大人”和“天命之所发”的 “圣人之言” I 。天命、大人和圣言三敬畏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它们根植于天的神圣性, “由一而三”形成儒家相对性的人本敬畏。
其中, 对天命的敬畏本属天的敬畏,因为天是中国传统中的最高神圣,乃是华夏早期文 明中的自然崇拜之一,但敬畏天命却是自然崇拜和道德崇拜的叠合结果。青铜铭文中的“天 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成王时《何尊》记周成王诰教宗小子,谓“ 昔在 尔考公氏克 弼文王, 肆文王受大兹令” A 。天在周初被道德化为“天命”,主要针对统治者而强调“敬德”和“保 民”B 。作为天人关系的核心阐释概念,“命”有“令”之意,“天命”即天之意志 C 。王者成 为“天命 ”的人格化 代表,但 天之“命”却 能随统治者 之“德”而 流转,即“皇天 无亲,惟 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D 。天之意志的命定论中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道德主体性,道德 由天人关系而获得规定,由敬畏而生成政治性的道德。关键的问题是,“德”与天命同出于西 周,根源于商周之际巨大变动,本意在于强调周天子乃“天”授之“天命”。只因“天命”并 非固定,有德者方可受命,失德者才失天命。此乃说明周初“德”字“不仅包含着主观方面 的修养…(还)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功夫,还包括治国安邦平天下” E 。至于“天命靡常,惟 德是辅”,这里突出的是天命,落实的却一个“德”字,践行的是道德。特别是拥有政治地 位的大人对维持天命道德秩序举足轻重,故而促使“敬畏天地鬼神的宗教色彩逐渐为政治所 主导”F ,大人及其德性也能够成为道德秩序实现的关键。这些“居高位者” G 或拥有政治治 理大权之人便成为价值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象征和代表,天命“有德”也就成为对大人的道德 要求。
因此,“天生、地养、人成”本来是一种生命论述而超越于道德之上,尽可为中国伦理奠 基,但其本身却非局限于伦理,它在天道 — 人道之间构成了后人敬畏天命的神圣根源。至孔 子强调“天生德于予”,即“君子”对事物中存在着的道德正当性的自觉,这种道德正当性的 根据即是“天命” H 。所以孔子自谓其“五十而知天命”,强调“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 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 I 由此可见儒家的天命敬畏乃是一种落实到道德秩序中的敬畏,敬 畏天命就是要有符合天命的道德行为,逐步形成“成己成物,参赞化育”的人生模式和 “天 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的逻辑(《春秋繁露 · 为人者天》)。于是,对天的崇拜转为对“天 命”的敬畏,以及对“大人物”和“圣人之言”的敬畏,方才能够完整构成“君子三畏”。
总之,敬畏在儒家中由天而始,一分为三,根源于天,继而伦理化为天命,由天命敬畏 分殊为大人敬畏和圣言敬畏:天命通过大人权力和圣人话语变为道德之神圣根据,大人与圣 言互相支撑以完成道德教化。在道德的信念预设中,儒家相信人性本善,人人得以为圣人君 子。这种信念预设极大影响了社会道德制度的形成和形态。而在具体道德实践中,敬畏及其 道德便以“礼”为载体和中介,能整合三大敬畏之人,便是所谓“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 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 万民以服” J 的圣王。如此,儒家三大敬畏便是一种自我 完善的互通结构: 拥有治理权力的大人(以天子为最高代表) 焦虑于失去统治权而敬畏天命,以“神道设教”使民敬畏并敬畏民心,最终形成儒家人本敬畏的特点及其礼教秩序。
诚然,天命之下即有神圣如圣人,拥有崇高道德并通达天道之人如尧、舜、禹。因为儒 家的终极价值目标是成圣,而圣人作为神圣话语的建构者,其重要功能不仅在于阐释天和天 命等神圣符号和内容,更在于对庶民大众进行道德教化,教人有所敬畏。所以在人本敬畏中, 经教化而成君子尤其重要。君子可解为人应有的道德人格状态, 是一种半强制性的伦理规定。 君子与小人相对存在而组成一个道德评价运作体系。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中包含了儒家基本的 伦理命令,所以“君子”必须相信“圣人之言”、跟随圣人并遵从圣人伦理命令。故君子人格 理想中蕴含了儒家秩序建构的努力,最终成就的是“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A 的道德信念。因 此,人只需要不断通过修身扩充自己的善良本心或道德本能,便能与天理同一,完成理想的 道德人格,与天地同参。如此,天命、大人、圣人之言便作为中国人的神圣对象,同时也成 为儒家人本敬畏的基本结构。
与儒家相比,基督教只有一个敬畏,即上帝敬畏。基督教起源于信奉摩西律法的犹太教。 摩西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律法性的信仰的结果,并且形成一种行动标准。因此,基督教由上帝 敬畏转向了对上帝诫命的敬畏。“敬畏”一词在基督教中仅指对上帝的敬畏, 这种畏惧不是对 现实事物的畏惧,而是根植于对上帝的信仰之中、超越了对现实存在物依赖性的畏惧,从而 神人之间的神圣关系能超越于现实之上,将神人关系提升到绝对的地位,并构成神圣的道德 法则。因此,基督教的第一原则是神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的意识也即对绝对的一与绝对 的原则的觉悟和遵从”B ,敬畏成为绝对意识而被绝对化。故基督教的敬畏是绝对性的神本敬 畏,从神本敬畏中生出基督教的道德信念体系。对神人关系的分析就成为基督教敬畏及其道 德心态分析的起点。
与此相关,基督教神人关系中一个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罪”。“罪”的概念中包含着 人触犯了上帝禁令的含义 C ,所以“罪”除了基于对上帝的敬畏外,还和上帝的诫命相关。 “罪”包括原罪(人生来具有的“罪性”),也包括因不信上帝、违背上帝律法等个人性的罪。 如克尔凯廓尔认为的那样,正是对上帝的敬畏和上帝的禁令产生了罪,罪又引发了其他类型 的恐惧,“通过亚当,那有罪性进入了世界。因为这个原因,这种恐惧就得到了两种类似物: 那在自然中的客观恐惧和那在个体的人身上的主观恐惧”。 D 在这种恐惧之中,只有律法使 人知罪并发挥对信仰者道德生活的规范与引导作用 E ,故敬畏的运作及其与律法的互动便能够 形成基督徒的道德心态。
由于人的“罪性”和罪是生命之存在的基本状态,有罪之人必将受到上帝的正义审判的 信念深入于基督教的道德心态之中。在神人之间的这种绝对敬畏关系中,敬畏就催动罪的意 识转向对救赎的渴望,进而产生“称义”的价值目标。“称义”就是指罪人之罪在基督耶稣那 里得到宽恕,人的灵魂得到拯救,这是基督教道德心态的基石。
虽然基督教的良心来自上帝的恩赐,律法来自上帝的诫命,但是良心会被私欲蒙蔽,律 法会因世俗腐朽 F 。这源于基督教对人性之恶、人性之软弱的信念预设。因此阻止人性恶的泛滥和律法的堕落成为基督教的主题,对道德人性的幽暗意识也极大影响了基督教文明中 的法律配置。因此,在西方人眼里,一个不信神之人乃是不可信任之人,也会被视为没有底 线、不讲道德的人。围绕着原罪及其救赎基督教展开了神本敬畏及其“罪感文化”的道德 图景。
为此,人本敬畏和神本敬畏的基本价值结构差异颇大。人本敬畏以天命、大人、圣言三 个神圣符号组成相对性的互通结构,并以“四端之心”之性善意识、成圣之价值目标、修身 涵养之道德行动构成实践理性的道德心态;而神本敬畏则以神为绝对原则,并以罪的性恶意 识、称义之价值目标、遵守律法之行动构成形式理性的道德心态,敬畏各自运作于其中发挥 应有之作用。
此外,二者在价值目标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深刻影响了二者道德心态之表征方式。其原由 在于儒家敬畏中的大人和圣人不仅成为生命存在的规则,还可以作为人的价值目标;而基督 教中神和人之间则有一道永远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敬畏对象本身是否为价值目标就成为二 者道德心态的一个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也导致如何“成人”( becoming )以及人如何“存在” ( being )的问题及其分别。
三、“诚明”和“信仰”: 敬畏的道德转化机制
儒家的敬畏心态是由道德状态所决定的构成性( being )心态,转化为对道德本性的完善;而基督教的敬畏心态是被律法所规定的存在性( being )心态,转化为对神之规则的坚守。逃 避是当人们在经历神秘的畏惧之时的第一心理机制。但当人们克服对畏惧的逃避,开始转向 畏惧,畏惧也就被转化。不管是儒家的楷模伦理,还是基督教的先知伦理,其目的都是将焦 虑性的敬畏心态进行转化。两种敬畏的道德转化机制不同,开出的道德和文化类型也不同: 儒家的敬畏心态是“诚”的转化路径,开出强调自我神圣的文化;基督教的敬畏心态是“信”的转化路径,开出强调规则神圣的文化。
“信仰”是对彼岸世界纯粹精神对象的超功利信服 A ,在基督教中仅指对上帝的无条件相 信和信奉。“在圣经的希伯莱语中‘信仰’主要是指律法上的。它是一种人在对契约和诺言的 坚守中表现出的忠诚和信任”B ,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这一传统,在信仰上要求以行动对律法 进行严格遵守,“人成义是因于行为,不仅是由于信德”C ,信仰和行动呈现出整合的趋势,这 一问题也是基督教神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儒家则不同,儒家经典中有“信”的概念,基本指 人际关系中的信用,《说文解字》解释为“信,诚也”。倘若与基督教强调对外在超越性的神 之“信仰”相比较,儒家在宗教意义上更为强调内在自圣的“诚明”,总是表现为现世价值信 念的特征 D 。
敬畏可以藉由神圣性和宗教性的不同呈现方式而表现出来,展开为日常性的道德生活 E 。 儒家性善论的意识以及人性通天命(性自命出)的神圣逻辑使其走向反省内求之路并追求自 我和天道的神秘契合;基督教性恶论的信念预设以及蒙恩救赎的神圣逻辑使其走向忏悔外求之路并追求和神之规则的契合 A 。因此,“诚”便成为儒家人伦中最基础的道德规范之一 B, 与之比较,“信仰”则成为基督教中最基础的道德规范之一。
在儒家相对性的敬畏关系中,相信人道德本能之力量的信念使儒家转向“诚明”的道德 工夫论, 即只要克己修身, 达到“至诚”的境界,“道心”自然充满, 为人做事自然妥当,“有 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诸己,所用莫非中理”C 。这即是说,要在“诚”中体现出对天道 的敬畏和依赖,成为圣人或顺应天理成为敬畏者的道德动力,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 者,人之道也”D 。通过将敬畏进行“诚”的道德转化,敬畏就能够被引入伦理关系中,并强 调“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E ,以敬畏为道德工具,为实现成圣的价值目标而“求仁之 方,日用之间,以敬为主”。其关键在于内在的诚,因为有诚,所以有敬,“须心有此恭敬, 然后著见”F ;因为有敬,所以有德,“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G 而“在‘敬’之中…… 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 H ,这就产生一种需要不断自我肯定的完美心态, 在其逻辑的驱动下必须发扬“诚”的品格来达至“明德”的终极状态。这样的一种道德信念
结构,使得儒家倾向将心诚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心”有不诚则堕入背离性善本性的不道德 状态,不可以为人 I 。在这种道德心态之下,儒家就发展出一种关于“明”的价值理性,这种 理性类型主要与情理智识有关,指道德心智的澄明无敝,能充分发挥本性之善,完成从敬畏 到伦理实践理性的道德心态转化。
在基督教的绝对敬畏关系中,由于罪的自我意识而渴望“称义”是敬畏者的根本道德动 力。“义人”即合神心意之人,是基督教对“好人”的一个定义 J 。这种道德意识离不开上帝 律法的作用,“律法的主要作用和力量就是将原罪以及其结果表示出来,并告诉我们,人的本 性能堕落到我们自己想像不到的程度” K 。但律法能使人意识到罪,不足够使人称义,因为 “人不可能不信基督而遵守律法”,也“不可能没有圣灵而遵守律法”。所以,“称义”不仅意 味着对上帝律法的敬畏和信守,更重要的是因对神之坚定信仰而获得的恩典,而“律法时常 控告人,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和罪,然而,福音却释放人,使人因着信靠基督,在神面前 得以称义”。 L 基督教的“信”不仅是人的主观行为,还是神的工作,并且“信就是信徒践行 律法的生活”M 。所以,“因信称义”是基督教道德信念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并最终成为良 心自由的基石 N 。虽然称义在根本上源于信仰神而获得的恩典,但并不意味着律法不再重要, 律法乃是引导基督徒开展道德生活并改造自我的重要规范 O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需要独自面对令人敬畏的上帝,并为自己一生的道德行为负责。在对神的敬畏中,个人感受到的是自我 否定,道德行为不过是增加神的荣光而已,故谦卑是基督教道德生活的重要心态,遵循神的 道德规则成为道德实践的核心之处。基督教中的虔信强调在敬畏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超越 性和神圣性加以理智上的认同 A 。在这种道德心态之下,基督教就发展出一种以神之规则为基 础的形式理性,这种理性类型主要与知识有关,完成从敬畏到伦理形式理性的道德心态转化。
由此可知,不同文化类型中的不同敬畏结构衍生为不同的道德价值类型及其实现方式。 儒家的道德基础是性善论的信念预设,关怀的终极问题是“成圣”,解决的核心路径是“诚 明”的心性工夫;基督教的道德基础是性恶论的信念预设,关怀的终极问题是“称义”,解决 的核心路径是“信仰”的理性生活。在不同价值所驱动的道德框架中,儒家的道德实践是在 伦理关系中的自我神圣,是自我肯定型的道德心态;与之相比,基督教的道德心态总是表现 为在神面前的自我抑制,是基于自我否定的自我治理技术。
四、道德差异 :循情理的“关系人”和守规则的“个体人”
儒家和基督教的道德心态中都存在着理性,只是二者的理性类型不同,前者侧重关系性 的实践理性,后者侧重普遍性的形式理性。两种类型的理性恰好对应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行动 者。以个人和上帝之关系为基础的基督教在强调信仰共同体和普遍性规则的特点之下造就了 个人 - 团体的社会结构,而儒家在强调家庭伦理和情谊的特点之下造就了总体神圣的伦理结 构。个人 - 团体的社会结构之特点是二者有明显界限,在团体中尤为重视公共规则的遵守, 成为公共交往的重要公德。而总体神圣的伦理社会则强调人伦关系而淡化公共规则,公德和 私德浑然一体。前者对应的是守规则的个体人,后者则是循情理的关系人。
绝对性的神本敬畏是一种以个体自我为基础的存在方式,强调人的灵魂在神面前是孤独 的个体。这是一种他者难以介入的人 - 神之间的神圣关系,所以自我首先是由神人关系所定 义的个体自我。在个体自我的道德心理层面,因罪而悔罪最后赎罪,希望在上帝面前得到宽 恕,于是人的行为被约束在宗教“理性”和“善”的范围之内,产生一种在心中独自面对上 帝的道德自律 B 。在这种个体精神之上,基督教进而强调团体之爱,促成灵魂独立之个体可 以在共同信仰的条件下结合为信仰共同体(教派)。罪的意识、称义的价值追求、个体化的 神人关系、依据律法判断善恶的标准、以信仰结合为团体的社会形式共同构成了基督教强调 良心自由、重视形式规则并区分公私的道德心态。这种类型的行动者可总结为守规则的“个 体人”。
相对性的人本敬畏首先是一种以关系自我为基础的存在方式。儒家重视家庭伦理,将其 视为道德根本并相信如此之信念:“我们自身绝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个体,而是一个经验中的 和实践着的人际关系的中心。” C 所以儒家的自我被伦理化,成为关系性的存在,由各种人伦 关系所定义 D 。虽然这种人伦关系中存在着天所赋予的道德正当性,人的行动需要遵循这种 正当性,但这一道德自我并不构想超越世间的形而上世界,只求在世间成仁成圣,并遵循以 “情本体”为核心的实用理性 E ,以等级差序的关系逻辑展开自身的日常世界。如果说“诚”是道德心态的内在层面,那么,“礼”则是道德心态的外在层面,一内一外构成了儒家强调礼 仪和情谊的伦理社会。在伦理社会中,个人道德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关系,道德原则随 着关系的不同而变化。“人情练达”,强调的就是以道德本心融洽各种情感关系能够成为伦理 社会之人的重要原则,涵养成为一种循情理的“关系人”。
循情理的关系人和守规则的个体人对于“好人”的理解尤为不同。在关系人看来,一个 好人应是通达情理之人,并以和谐人际关系作为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关系人的一些道德原 则甚至无法言传,仅是一种实践性的存在,需要自家“体贴”出来。而在个体人看来,一个 好人应是具有信仰,并遵守规则之人,这些规则可以被理性化而成为知识性的存在。当然, 循情理的关系人和守规则的个体人仅仅是一种文化的理想类型,与现实的实际存在之间存在 着相当的张力。
五、“文明互鉴”中的敬畏结构及其转型
儒家和基督教的敬畏结构不同,两种敬畏造成的价值类型、道德信念也存在差异,但都 旨在建构向善的人心秩序和正当的社会秩序 A 。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的生命之存在应 如何与敬畏关联,以达到更高的价值境界,故二者虽在敬畏对象、敬畏形态和敬畏方式上多 有不同,但仍然有互通和互鉴之处。
从敬畏根源上来看:儒家的敬畏是“三元一体”的秩序框架,强调敬畏天命、敬畏大人、 敬畏圣人之言,它们分殊的同时又整合为一体。而基督教的敬畏根源则一元化的,敬畏就是 敬畏上帝。不同的敬畏根源又衍生为不同的敬畏方式:儒家强调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的身心敬 畏,基督教强调在宗教生活中的规则敬畏。在生死心态方面,儒家强调“生死之际、唯义所 在”的敬畏,基督教则强调对生命本身的敬畏等等。
比较儒家文明来说,基督教神本敬畏值得借鉴的要点有二。一是由人神信仰关系中介机 制而生成对普遍性规则的敬畏,二是基督教关于人性的幽暗意识可对性善信念的负面影响保 持警惕。总之,不同文明之间理性交往,取长补短,互相借鉴才是未来人类文明继续前进之 路。这些差异和共识的要义在于:在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应当敬畏何物?敬畏的结 构如何转型?这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道德心态和文明秩序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明互相借 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