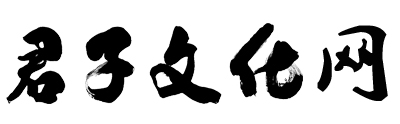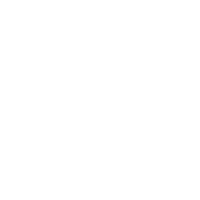先秦儒家的君子观念及其社会意义
——世俗生活中的良善人格
邢文正 硕士 南京大学
摘 要:在先秦儒家共识性观念中,君子是集理想性、经验性、世俗性于一身的存在,他们在怀抱“士志于道”之理想的同时,又积极与世界互动,以避免理想堕于伪善。在此意义上,有“君子不器”“修己以敬”“义以为质”“颠沛必 于是”四重精神准则支撑君子的光辉气质。从事实的角度看,虽然社会稳定多数时候靠的不是君子,但那些作为良善主体的君子和具有温厚情怀的君子依然发挥了促进美好、维系生存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士人政治中,君子是社会整合、协调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君子”是先秦典籍中的常用表达之一。在个体生命与国家治理的双重意义上,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大致都会不遗余力地论说它、描述它,这样的道德理论早已被认为是中国思想的一个核心化特征。今天,与体系严密的西方学问和现代知识相较,中国的传统之中没有精细化的学科体系,似乎也缺乏必要的“实证性”与“思辨力”。与此同时,人文学 科的价值表明,一种合理的道德既非说教,更非训诫,而是基于特定语境、立足现实关切,以回应现实之中的重大问题。以此,若要追溯中国思想的文化深厚性与现实指向性,就不应止步于道德理论本身,而要回到古老的观念系统,去观照道德理论的提出者尤其是儒家诸子的问题意识,深度理解他们的关怀和感受。值得申论的是,近古以来,人们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对儒家的道德理论进行了重构。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那些针对“儒家哲学”的现代说解,虽然在心性论向度不断深化,可一旦回到中国思想的原初问题,它们很大程度还是会囿于特定的概念框架,如重德轻位之分、文质相成之理、仁礼并举之义等,难以与儒家诸子的问题意识全然呼应、匹合。黎红雷说:“后来的儒学研究,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礼学’和‘仁学’上面。”[1]故反以思之,面对这样的文化现实,需辨析和解决以下问题:1)按照先秦儒家的共识,什么是道德“君子”,什么是伪善小人?2)这样的君子人格是如何成就的?3)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君子的作用,社会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君子?解决这样的问题,是理解中国思想的核心与关键,也是关切人类现实境况的应有和必有之义。
笔者尝试以儒家的“君子”共识为理解背景,梳理“君子”在儒家经典文本中的大致特征与形态,以辨析人应如何成为“真君子”,进而结合史家研究印证君子在中国社会所呈现的意义,并说明士大夫文化遥承“轴心时代”,起到整合、协调、范导、引领中国社会的良性效用。
1 良善与通达的君子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也是古人论事的惯用表达① 。从儒家文本看,“君子”的来源丰富而多样,内涵具体而复杂。如《尚书》和《易经》中的“君子”不同,《易经》和《左传》的“君子”观念也相 去甚远。对此,时下的研究成果颇多,识者自参①。别有意味的是,从思想演进的历程来说,今人大致会同意,先秦儒家各派别存在一些基础性共识。先秦的儒家知识人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景,也有相通的价值范畴体系。《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2]98 实际上,除了传述经典,儒家自孔子以来就尝试描述和呼唤君子,并以行动呈现君子精神。无论后世儒家如何异趣、如何相訾,君子的一些品质始终是他们矢志追求和不渝坚守的。经时间的积淀,“君子”在后世常识中的基本蕴含得以奠定。
笔者就“君子”概念的理想性、经验性、世俗性作一些疏解,以见它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共识性、深厚性和启明性。就质地而言,君子不是随顺潮流、屈曲柔弱的存在,而是要树立生活的价值、社会的目标、政治的原则,以衡量、批判、改善、提升现实世界。通常来说,“信而好古”“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是先秦儒家的价值基础,而这样的“古道”或理想很大程度上既是议政传道的内在支柱,又是立身行事的标准与原则。关于这种理想性的君子,《论语·述而》中孔子和子贡问答的一段话颇具表现力和阐发力。
(子贡) 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3]179
这是儒家有关君子之理想性的代表说法。正如《论语》中显示的,君子的最基本特征是信守“道义”、通经致用,因此,他们在立足人世时,必须坚守“仁义为本”的原则,即便结局悲苦,也会“生生不已”地成就理想价值。相反,若行为主体放弃和抛开“道义”,以不正当的财富和地位为目标,则必然会引发价值系统的淆乱、泯灭生命之中的良知与德善。故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180实际上,综览儒家文本,这种追求道义卓然特立的人格形象在《孟子》《荀子》《易传》《礼记》里都有呈现,孟子谓之“大丈夫”,荀子谓之“刚健不苟”“坚刚不屈”。以此,在儒家的共识和通见中即有不少富于德性意味的“君子”说法,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3]164;“笃志而体,君子也”[4]38;“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4]179。凡此之类,其共同道理是君子须熟谙现实生活中文、礼、道之类的知识,更须在意趣、行为上“笃志”和“不苟”,如是,方能明晰事理、洞察原则,以合乎“君 子”之名(详见后文)。
就存在方式而言,君子是文明社会中经验的存在。按照今人的说法,在中国思想中,人若想得道,就必得关切和理解生活,不是在彼岸世界中反复追寻理念与形式,而是面向尘世经验,以生命去承载对“道”之反思[5]150 。因为有这样的精神趣向,故“君子”也食人间烟火,亦有情感寄托,他们足够真实,让任何人都可以感知、接触、模仿甚至达到,即所谓“言为可闻,行为可见。言为可闻,所以说远也;行为可见,所以说近也”[4]598-599 。以此而论,可知君子的“言行”之理之义,也能为人们所亲证,进而为他们所学所鉴,此即荀子所说的“诚于内而发于外”;“德至者色泽洽,行尽而声问远”[4]598 。
在人类精神历史中,这样的君子是真实存在的。从《论语》记录的孔门言行看,孔子和七十子大致是一群经世致用的君子式活动家②。稍稍熟悉《论语》即可知颜渊、子贡、子路等无不是面目鲜活、性格粲 然,如“闵子……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3]260,就连孔子本人,也是“申申如也,夭夭如也”[3]172,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对子贡说笑、指原壤笑骂、对子路发誓表白[3]124,352,165 。重要的是,儒家“君子”的生活相当健康,这不仅蕴藏醇厚朴茂的人生态度,也表征君子人格的真实和真切,更启示所有人自我成就的路径与可能。
基于此,就理想的实现途径而言,君子不是如神职人员一般视“道义”为令人炫目的永恒理念,而是从世俗性出发对具体情境中的价值实现寻求变通性理解。从概念的基本义角度讲,“理念”敉平了经验的复杂性和世界的多元性,是以一种抽象的道德范畴衡量和判断人的行为;“世俗性”旨在对具体情境中的“ 自然之理”进行理解和深究,人可以因此而通向社会,行走人间①。先秦儒者尤其是荀子一系都会重视这种“世俗性”的君子。他们有理想、讲道义,但这些离不开对事理的认知,离不开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的互动过程。在此意义上,君子必须四处奔走,以足够的阅历构造开放的道德和原则,终而在活动中理解、展现、传递善。《荀子》说: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4]304-305 。
荀子精于政治的设计与运作,认为正义不靠理念中的善恶认定而成就,君子必须以理性和批判的分析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世俗性的理解意味,荀子在其他地方以“知类”说明。故无论是在逻辑还是在事实上,“士人”真能“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在行动结果上才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4]179;亦唯如此,在精神面貌上才具备成为君子的基本品质。况之后世,士大夫们多把“内圣”当作“经世致用”的唯一根源,以致道德判断代替了活泼的、对现实世界的观照。于是,士大夫在政治实践里,一方面,试图以道德判断“弘道”,积极主动地制约权力;另一方面,这样的道德判断却又不断为权力所“利用”,使权力在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外衣下做着自私自利、欺世盗名的勾当②。
从君子与民众的关系来看,君子会以温厚的态度关切和包容人在现实中的缺憾,进而与他们一起完美。如上所论,君子的基本素质里蕴藏了世俗性的精神趣向,它要求君子摆脱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理性分析。在世界多彩、人性复杂、善恶“俱分进化”的情形中,由于缺憾必然存在,故君子一定要反思如何面对恶,如何把恶的变成好的。在这里,儒家走的是“假恶济善”之道,即君子会以巧妙的方式善用人的欲利行为,使这种“人欲”作为人生行动的基础,在结果上创造、促进、扩展和成就善(详见后文)③。惟其如此,君子与民众的互动才是良性的,人与人之间才会少一点道德专制,人才会得到温暖、有趣、洋溢着生命力量的生活。
进一步而言,君子一旦遵循“假恶济善”的方式和途径,这种方式和途径之中,就充分显现了君子的明理与宽容。正如孔子所论:“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3]286 僧侣式的卫道士往往会拉上道德理念的旗帜去衡量和判别他者,于是,合乎理念的,便是门徒;不合理念的,骂成“禽兽”。因此,反以思之,君子应该客观地、切近人情地、现实有效地对待所遇。故荀子曰:“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4]504进一步,在君子如何与世界互动的问题上,儒家主张“尽其情伪”,宽容爱人,即君子必须洞察经验,进而去接近复杂动态关系中人的真实,尽可能充分理解和成就他们。这样的要求和《论语》中“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路向本质相通。也正因为此,君子才能有效地亲近和融入民众,进而才能利用民众的力量成就人类之“公”、社会之“义”、“天下之事”,即所谓“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4]100-101 。从君子的生命进程来看,这种以明晰事理的态度宽容他者的行为是他从人格保持到人格扩充的进展,也是他从个体内心走向公共社会的精神跃动。
下面,笔者以上文梳理的“君子”涵义为理解背景,对儒家文本里成就君子的准则作逻辑考察和辨析,说明成就君子的这些准则范导他们的世俗活动,积累丰厚的文化资源,而作为载体的君子促进着人类的共同美好,乃至影响后世帝国的政治与历史进程。
2成为君子的准则
通检先秦儒典,“君子”这个名词,太过普遍、繁 多,而有关“君子”的理解时常简要、抽象。后人多以“道义”“文质”“仁义礼”去理解“君子”的精神特质,故对“君子”的说法往往头绪纷繁、驳杂不堪①。实际上,从思想的共识层面看,“君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内核之一,在孔子那里得到了最为凝练的表达。《论语》里,有 4 点“君子之则”,即君子不器、修己以 敬、义以为质、颠沛必于是,是基础性的,是可以推导君子的其他品质的。这些准则的意义与《荀子》《礼 记》的“君子”之说息息相通,它们呈现的价值丰富、多元,而又联系紧密、层次历然,共同塑造了后世常识中“君子”的基本蕴含。在此意义上,就“君子”之 说的共识性、多元性、逻辑性而言,今人的研究与判断似乎依然有推进的空间。这里试对“君子”的 4个层次作一些说明。
2.1履行职能的原则—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载:
子曰:“君子不器。”[3]61
在儒家语境里,“君子不器”为君子明晰了行走 人世的基本身份,并启示了君子践行这种身份的方式与原则。与先秦其他对君子之“行”与“事”的理 解相较,“君子不器”之说显现无与伦比的高贵性、现实性与深厚性。从先秦儒家共识层面看,“君子不器”至少有两个向度的内涵。
先看第 1 层。《荀子 ·儒效》中的一段话最近乎后人理解“不器”的常识。
相高下,视墝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樽,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4]145-146 。
做专业的、技术的事情,君子不如工、农、商贾, 甚至学者;君子之所长应在“事变因应,曲得其当”上[6]125 。从人在社会中的情态来看,这里的“专业化”指向的是技术分工的不断强化,也是广泛文化的逐渐流失;是职业化生存的不断凸显,也是人文体验的每况愈下。因此,在荀子看来,君子需要“明理”,去观照人类的真实经验,在人文意识遭到弱化和贬损时,他能及时关切生命、协调“万物”。进一步地,这样的君子忧心于社会的生存与绵续,更关怀社会治理的各项事务,故他们会主动出仕、奔走、立言、施教。正是这样的关怀与担当使超越了具体专业和工作的君子形象在传统社会里焕发光彩,使君子成为维系社会的“脊梁”性力量②。
再说第 2 层。《礼记·学记》云: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学无当于五官,五 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7]469。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7]469 。
这两段中“不器”与“学”的说法可以视为君子成为“社会脊梁”的基本方法与途径。就此而言,君子关怀社会虽然重要,但怎样关怀才是关键。与西方按部就班的契约观念不一样,中国式的君子具有的是“顺乎情理”的精神,他们需要知道世界的情态与社会的质理,从这些“情理”出发,才能“循理而为”“利用厚生”。因为在中国早期思想中,“君子务 本”[3]30,按照古人的本末之理,符节券契、一纸文约不过是君子生活中的器具(“器”)和枝节,是“末”;而知悉事理、“比物丑类”才是君子之为君子的基本要义,是“本”。所以君子型的人物会以“务本”的方 式进入世界,思虑以最好的方式面对“理”,进而择善而行、呈现公正。需要说明的是,《礼记》中宗族“恩义”的说法,如“旁治昆弟,合族以食”[7]429,“系 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7]431等,即体现了对道义、德善、应然之理的认同与接纳,传统的君子形象因此也得到人们的景仰和敬畏。
综上所述,在儒家那里:1)君子的身份感源自超越特定 的技术 或 职业去看世界、做“脊梁”。2)君子看世界的方式其实也是“不器”的,即君子不是依凭契约规范处理问题,而是回到问题本身,通达事理地行动。那么,从自我生命出发,君子应遵循何种原则、通过什么方式成就“不器”善质呢?
2.2面对自我的原则—修己以敬
《论语·宪问》载:
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 而已乎?”曰:“修 己 以安人。”曰:“如斯 而 已 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3]351
“敬”这个词在儒学史上颇为常见,后世对“敬” 进行哲学化理解和阐发,论者颇众。但在先秦语境中“修己以敬”启示的是君子面对自己和他人的基本原则、从自我出发走向他者的必要与可能。就表述形态而言,《论语》《荀子》《易传》中带“敬”字的语句大致涉及具体的人生行动,其基本意思是,人在待人接物时对不可放弃的价值和原则要心怀敬畏。这种行为心态的蕴含在以下表达中体现得颇为明确。
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3]145“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8]60 。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4]301。“言忠信,行笃敬”是儒学的要求之一,也是历来君子的常态,史传中记录的君子典雅而踏实。上引《论语》和《易传》的两句话,一句以反问结尾,一 句以描述直陈,其共同主旨是,君子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应向着正向的目标,以“敬”为务,“言无所苟”。
实际上,儒家更为圆熟的“敬”观念在荀子那里。上引《荀子》之文,表面上是说要敬畏他者,尤其是畏惧“不肖者”所产生的危害,故有“畏而敬之”“疏而敬 之”的说法。但按照时贤的精审分判,敬与畏是不同的,“敬”是人应对万物的中正之态,“畏”则是源自人 的生物性本能;“敬”意味着光辉地前进,“畏”标志着 在危害面前“退止”①。因此,荀子说“仁者必敬人”, 其实关键在后面的几句话,即“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忠信端悫”是“敬”的本色呈 露,“而不害伤”是为“敬”者无害于人的底线原则。从这些表述去理解,“敬”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心怀原则而待人处世,即所谓“以义变应,知当曲直”[4]48 。
需申论的是,《论语·宪问》中孔子和子路的后 续问答清楚交代了“敬”的目的、方 向与效用, 即 “敬”不只是面对自己、敬畏原则,还蕴含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责任,并着眼于社会良性意义的建构,故孔子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也正是在这 样的意义上,血缘亲族的义务、社会交往的要求、责任的约束使君子的人生经验开始拓展,他会主动反思:当“我”充分敬畏原则之后,“我”的“修己”行为 如何能切实“安人”,如何能对他人有益,如何人己俱成?而在提升自我和面向世界的要求之下,“义”作为外向性的德性,被儒家诸子努力阐发和追求。这样,在复杂和多样的社会情境中,“守义”的君子从恭敬笃实的修行者变成可爱可敬的活动家,而且有了理解、分析、判断、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与能力。
2.3面对他人的原则—义以为质
《论语·卫灵公》记述孔子说: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3]365
这是先秦儒家有关君子特质最为全面的一种说法。从语意上讲,孔子以具体和平实的口吻为君子呈现和确立了一个多元价值体系,各种价值和多元理念(义、礼、逊、信等) 因此被匹配—这样的多元理念是《论语》文本的常见表达,也是古今公认的儒学精髓。但若注意到上引文本中“质”是“质地”或 “根基”,“之”的内容指代“义”,则孔子的“义以为质”清晰地展现了“义”本身的意义、功用、力量与根基性。这个“义”说明的是君子面对他人的应然态度及其与人互动的基本方式与原则。
一般而言,《论语》之“义”是指人之为人的本分、义务和责任,是指这些责任中具有的正向性价值取向。在儒家有关“义”的定义性说法(如“义,理也”[4]580,“义者,宜也”[7]702,“行义以正”[4]559,等等)中,“义”的中正取向跃然。从概念内涵的角度讲,“义”的基本义是事物有其成为自身的基本之理,其衍生义是事物有其必须遵守、不可突破的边界和底线①。这个边界和底线对自然万物或人而言,都是合理的、合宜的。就人而言,在“何以成人”的意义上,自然人必须坚持以这样的底线和本分规约自己,成为文明的社会人,与他者正常沟通,平等对话。正因为此,在“义”之为“正”(应然)的意义上,儒家开始把“君子”和“义”匹合使用,即君子要以“守义”的姿态处世和健行。不论是在欢欣还是愠怒的情形中,君子这类良善主体都会以“义”为目标,真诚并真挚待人。此即“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3]108,“君子义以为上”[3]417,“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4]42 。这些经验化道理具体、实在,启发力颇强。所以从先秦儒典中对“君子”的“通见”来看,“君子义以为质”涉及君子的价值导向问题,即必须以“义”为本,才能成为君子。
更为重要的是,“义”在先秦语境中不是抽象的道德境界或良知全德之类,而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更是人从底线出发对合乎底线不逾边界的“人欲”的包容之态。即“义”者是遵守底线的,但他们在明晰和坚守底线之后,依然不拒绝“利”,依然去接纳那些正当的合理的利益。这样的意味在先秦儒典中被呈现得淋漓尽致②。《荀子·不苟》曰:“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4]46在古人的“取舍”之理中,欲利行为只要不突破底线就可以被宽容和允许,触及底线(“义”)时才要“不为所非”。就经验与实践层面而言,“为非”在生活中的作用是伤害与损耗,故必须严加控制;而“欲利”与“畏患”发挥的是中性无害的作用,如若加以禁止,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偏执,进而会削弱甚至是伤害公义。所以君子一定要主张和维护“欲利”。《论语》里孔子盛赞子产“使民也义”,很大程度上也包含这样的意味。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思想的经典说法“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4]448 。敝屣人欲其实为“不义”,而善待和善用人的欲利行为才是君子所必需,“义”者所必为。同样,在《荀子·正论》中,宋钘排斥欲望,认为欲利不“义”,而荀子持不同意见,说“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
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4]407。意思是,古人不认为“利”是不好的,而认为“人之情”喜欢“利”多,不喜欢“利”少,故设立赏罚,以教人向善[6]390 。以此,在儒家君子那里,真正的“义”不再被抽象为“利”的对 立面,相反,“义”可通过接纳并善待欲利行为实现,即导利本身就是行义。这种直面和善用“欲”与“利”的思想蕴藏着君子精神里开放对待世界的力量,这是关切现实生活的基本起点,是抵御道德审判的最好资源,是人有效相处的保障。而在开放面对他者的意义上,君子开始逐步与世俗联系,最为关键的君子特质—世俗性(详见上文)因此有了实现的可能。
简言之,“君子义以为质”不仅是为了遵守本分,更是为了面对世界。面对世界的过程,需要的是接纳“人欲”,呼唤的是朴茂态度,关键是走向社会,目的是有益他人。而因为工作与活动,以面对世界为基础的“义质”之中,映现了君子与世界之间活生生的互动关系。这样的“义质”是儒家式君子的根基与底色,也是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德性资源与行动力量。
2.4坚守良善的心态—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曰: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3]104 。
这句话带给中国文人无限的力量。况以史传中的君子人生,则它明晰的是君子在逆境中负重与付出的心态。需要说明的一个事实,在现实情境中,君子往往不得善遇。从史传和儒经的丰赡记载看,身处权力中枢的精英人物大多也是普通人,甚至只是粉饰太平的“司仪喝彩之流”[9]38。而儒家倡导的贤人君子却未必身居高位,更不能叱咤风云,其人生处境大多艰难、窘迫、惨淡、卑微。如在《论语》中,孔子在陈绝粮,史鱼以尸而谏,柳下惠多次遭黜,乐师们流转四方[3]355,358,420,427 。故荀子曰:
君子能为可贵,而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己……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4]120。
君子可以修己、守信、有能力,但不见得被尊贵、被信赖、受任用,所以君子不为浮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怯馁,不因外物而动摇偏侧[6]102 。儒家式君子之所以能在困境中坚守道义,根本在于他们不懈“求志”“求仁”的态度。实际上,儒家诸子基于经验 智慧,自觉地意识到困境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故孟子宣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10]358 因此,君子在重重困境、累累艰难之中也会乐观而思、无畏而行。他们会以坚信甚至是捍卫仁义的立场在逆境中为他人奉献温暖与良善。《论语》曰:“君子固穷。”[3]355“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 而免。”[3]158“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3]425儒家式君子相信“道之不行”这个事实,丝毫不妨碍“率道而行”的必要与可为,更不妨碍君子的光辉与不凡。在这样的意义上,道义、良善、信念和爱支撑着君子的无畏精神。
就道德的内在要素而言,相较于“君子不器”“修己以敬”“义以为质”,“颠沛必于是”毋宁是一 种宗教性的信念,其典型的追求目标是心灵寄托与人格完善。在概念内涵上,它关乎良知、热情、信仰 和境界。于是,道德信念似乎成了“君子”行为的中 心本体,此即孟子所说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10]362 。仿佛对这种信念的践行不需要经验和阅历,更不需要对事实的理性分析,后世高扬道德信念的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生活,也远离了先秦的“君子”理想①。但在先秦儒者那里,这些信念起到的只是范导性作用,即引导君子进行世俗活动的作用。与社会上的普通人相比,若没有这样不屈不移的刚健风骨,那些君子又怎么能扎根世界大地,分析并改善他们所处的现实呢?
必须说明的是,在儒家文本中,“君子”的精神准 则并不只有以上 4 项,还有“君子威重”“君子知命”“周而不比”“君子求诸己”等,参照《论语》便可了然。笔者之所以从这 4 项入手分析是因为它们对其他精神内涵有决定性意义,如君子守义不苟, 自然能“知命”和“立命”,合理合情地面对“天命”;君子以敬修 己,必然会“威重”而笃厚,“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3]164;君子明晰了信仰的地位、归属和意义,一定 能“求诸己”,而把宽容和德善留给他人。就此说来,它们是基础准则与衍生准则的关系。这样的准则丰富、多元、切实—正是因为这种切实性,它们贯穿中 国“君子”的生命。而作为良善主体的“君子”和具有 温厚世俗性的“君子”,则因此发挥了促进美好、推动 进步、维系生存乃至构建秩序的良性效用。
3烛暗彰微的意义
从中国传统文本上讲,“君子”这种人格,不论在现实中多么稀少,大致都会被知识人所强调和重视,并被他们所呼吁和阐发②。从历史和实践层面看,这样的君子似乎很少是历史的真实,而更多是道德的理念。所谓的“贤人政治”,实际上不仅是于史少徵的“神话”,更是充斥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可是,即便人类的境况如此,中国式的知识分子依然相信“君子”十分重要,更值得尊敬。用孟子的话来说,否认君子诋毁良善的行为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行为[10]286-287。
人类发展历程表明,政治—社会的稳定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稳固而开放的制度结构。历史上具有开放性的体制和秩序,都不会强制社会人内心改造、道德“进化”,相反,它能够善用社会人的自保、欲利和自私行为,在客观上维系政治—社会的平衡与发展。如投资理财是基于欲利目的,却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③。换言之,在人类历史和现实当中,“私人的恶德若经过老练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可能被转变为公众的利 益”[11]312。虽然人类社会的常态格局是“善”与“恶”并存、不平等与秩序化共生的格局,但正因为有一套“假恶济善”的机巧与规制存在,那些“恶”才不会纵 情肆虐,人类社会才能绵延而不至于土崩瓦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性真实所在。
因此有了一个关乎文化之深刻性、价值性、生命力的问题:既然社会的正常运转靠的是体制而不是君子,那么中国的思想家苦心孤诣地论说、呼吁和建构的君子人格,从政治—社会层面上看究竟有何种意义和作用?
君子的良性意义是他可以向世界呈现善、传递 善,与世人共同完美。人类社会依靠“假恶济善”的 体制维系的事实,并不代表体制本身是无害的,更不意味着体制可杜绝所有的腐败和不公。因为即便是足够合理的体制也会潜在蕴含各种不平等。从这样的不平等体系出发,“有余”阶层往往可占用多余资 源,隐秘伤害公正。即制度体系本身已同时蕴含善与恶的可能。对于此,任何人可在经验中明晰和体味。故从正向的角度说,人类之所以能够奔向幸福,绝不仅仅是因为体制和规范,也有赖于人们对良善自身的接受、认同和实践。按照荀子所论,“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4]56 。这个“诚”是人类追求美好、积累社会之“善”的醇厚资源, 也是他们摆脱伤害、拒绝体制之“恶”的底线力量。
进一步而言,在儒家那里,君子是人伦道义的载体,更是烛暗彰幽的“完人”。就现实的具体情境而言,尽管有“假恶济善”的体制存在,已经能维系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秩序,但君子的目的与志趣依然是使世界美好,是在与世界一起生长并育的同时尽其所能地有益于它。故《论语·阳货》中子游在武城推行教化还自作解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3]402这就是君子的增益良善之道。正如先秦儒者的“通见”所显示的,君子增益良善的方式不是强制性灌输和训诫,而是要精通事理、练达人情、善担社会责任。君子要“知事”和“明理”,才能“化民成俗”“利用厚生”。故《礼记·檀弓下》中,赵文子遵循“ 自利利他”的路向,“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7]144,为国家积蓄人才力量。到了汉代,即出现了温良沉厚的“循吏文化”,如兒宽“迁左内史”时“劝农桑,缓刑罚,理狱讼……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12]2629-2630。韩延寿为东郡太守,在“行法”之余“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表孝悌有行,修治学官”[12]3211 。故在经验和逻辑的双重意义上,君子的教化意味里承载着君子自身的启明性效用:君子就是指引人类前进的明灯,可以在现实、体制、法律、规范中补偏救弊。
君子的良性意义是他在危难之际会成为扶危救困的积极力量。由于一种体制不能解决任意的问题,和平也不会毫无悬念地出现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段,君子在体制崩溃、社会危机、人类遭遇困境时发挥着重建秩序、维系生存的作用。据笔者所见,《论语》里曾子所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3]201,最简明也最清晰地显现了“君子”的“救世”意味,在后世的诠释中,这句话不知被多少人所咏叹、比附和联想,如伊尹、周公、诸葛亮等都成为常用例证[13]679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咏叹和理解本身不仅意味着君子人格的可敬与可贵,也表征了传统对“君子”理念的认同与重视,更彰显出普通人对典范君子的眷恋和思慕。
从人类生存经验看,君子是常人所必须依附的温良资源之一。按照一般的情境化理解,普通人在遭受困境时往往会渴望公正地获得利益,因而渴望出现君子或公正之载体。因为他们能利用君子的奉献(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满足自己的需求。就人类社会层面而言,这是常人面临危机时的一般心态,也是他们在危难中维系生存的必要选择[14]27-28 。以此而论,可以说温厚和明智的君子正是凄凄惶惶寻求安全者的避难之所。而当寻求安全者归附时,君子又总能不负所望地保护他们的生存,以求建构秩序、臻于和平。按照史家的说法,魏晋衰乱之时,村坞集团的贵族“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救人于危难,施人以恩义,以深受众人仰慕的人格而成为领袖……这里存在着一种以道德意识防止成员间纠纷,维护集团生存的意图”[15]89-91,前论君子“因众成事”的行为在这样的“集团”中光辉尽显。
至关重要的是,人们对君子或良善的渴求并不能必然导致君子存在。普通人处于乱世危难之境,往往都只能以一己之力,默默捱受苦痛。但社会发展经验表明,君子或有教养者确然存在,更是意义非凡。
综略而言,君子在体制能“假恶济善”的时代会保持道义立场,摆脱现实谬误,改进庸常生活,推动良善和进步;在体制失去效力的时代,君子又会以温厚的方式接纳民众,为社会积累必要的秩序与德善,进而为人类带来重生的可能与希望[14]29 。历史上,这样的君子人格光辉灿烂、可亲可敬,如孔子、董仲舒、王夫之、章太炎、邹容等都是这种君子的典型。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指出,君子与中国社会血脉相关。在时代发展缓慢、过去与未来联系的传统情形中,统治者无法忽略社会的固有特征,更不能无视君子的良性意义。在这些意义上,君子之存在是中国传统的特殊要求。
(西周时代)“君子”这种特殊社会角色是尊者、亲者、贤者或君、父、师的三位一体。“君子”的义务不仅是作为统治者而施治,而且还要“为民父母”以施爱,为民师表以施教……在封建士大夫所承担的“礼治”之中,业已孕育出了“君子治国”的贤人政治理想,这一点在后来就成了帝国时代士大夫政治的基石[16]468-469 。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是经由周政、秦政、汉政、新政这一系列复杂曲折的政治变迁过程之后,而演生出来的。当政治文化的发展使“礼治”把一度分立的“法治”重新纳入了其统 摄约束之下的时候,业已充分分化了的政统、亲统和道统就再度一体化了……“君、亲、师”之三位一体关系,再一次地成为王朝赖以自我调节与整合社会基本维系,并由此而造就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专制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君子治国”之政治理想……也就一直维持到了中华帝国的末期[16]477。
如前所论,虽然秩序是依靠体制建立的、体制的核心目标不是美德,虽然君子无位,但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毕竟承担了某种“君子”职能—阎步克所说的士大夫政治,在古代逶迤发展,呈现了与中国社会的协调性、适应力、匹合度。在这样的政治中,具有人文精神和伟大力量的君子成为中国社会改善所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