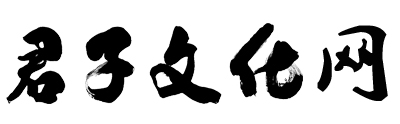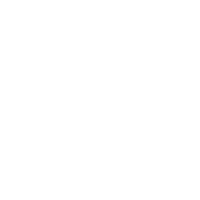关于君子人格与好汉卫国的最初想象
——《樛木》与《兔罝》的悬置与对比
温左琴 副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
在世俗想象与儒家理想中,文能兴邦、武能定国该是不世奇才,谁不期许?那在我们民族最早的咏唱《诗经》中,可有此种理念的发酵与彰显?或者说,我们民族最初的君子人格与好汉情怀是怎样表现的?《周南》 中的《樛木》与《兔罝》可做如是观。何为君子?儒家那里自然有很多说辞,但我们从《诗经》这里一路读 来,却有太多感慨。我们甚至不知是先有《诗经》之召唤,还是先有儒家之建构。但在一种社会整体期待君子的声音中,我们不能不想到某种层面的缺失,抑或就是旧时代的分崩离析,使得昔日的礼义廉耻带上梦幻,成为想象,对其的回望与坚守也便成为必然。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所谓的礼乐之邦,大同盛世,不只夫子梦回,我们更在《诗经》的不断阅读中,感喟并叹息。《樛木》就是此类情怀的抒写,极深情,更惆怅。我们不知是旧 梦重回,还是新梦继续?我们又想问:如此倚重某人,可他真能担当?我们不愿他过多负累,劳苦终生。《兔罝》似乎就此做出回应:那孔武有力的猎人,不只是他,更可能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于细微处,彰显其雄才大略,可以依托。下面我们来细读这两个文本,看看它们在悬置中又做出怎样的对比?先读《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 福履绥之。
何为“樛”,《毛传》解曰:“木下曲曰樛。”就其诗旨,《诗序》云:“《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 嫉妒之心焉。”我们姑不论此种解读或比附有无根据,只想想大自然中有这样一种存在,姿态如此之低,甘为他物做护佑,不能不心生欣羡。朱熹《诗集传》引东莱吕氏曰:“樛木下垂而美实累之, 固结而不可解也。”戴震《补 注》更直接明了:“樛木,下美上之诗也。”看来此种心思,人皆有之,只是不知何人才配得上此种尊荣?何楷《古 义》:“《樛木》,南国诸侯归心文王也。”这种解读自然是注意到“周南”之地理属性,或该篇可能会有的诸侯来朝的壮观景象。《诗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所以凡咏文王之德者属雅,咏后妃之德归风。若该篇真是咏四方来朝,南人服膺,则该入雅,不应作风。可《樛木》作为《诗经》或《周南》中的第四篇,自然是风之始。那该篇入风,究竟缘何?颂雅诸侯真会作此乐调?况且此“木”在南,若是比附文王,何须做这样的地理强调?所谓南面之王,跟该篇之诗旨,更是相距遥遥。其实我们仍然无须深 究这些,我们只要知道,该篇之周南,确实是不同于北方诸国的存在,它意义所涉的江汉流域,于诗篇,我们更想把它当作是有别于此地的彼地或异域,甚至就是一种理想的存在。就此,我们再看“南有樛木”时,不由心神恍惚。后面之“葛藟累之”,竟让人屏息。这究竟因了什么?我们继续细看:
樛木,就字面而言,确实应指枝条盘曲下垂的大树,类福建的大榕树,而自然不同于《周南·汉广》中“不可休息”之“乔木”,虽然它们都有一种开篇咏叹的意味,但“乔木”即便挺拔高耸,怎就不可护佑别的植物? 我们来看“葛藟”,据说是野葡萄,蔓生植物,可食用;也说是葛麻,可织布。无论为何,可以攀附,可以成长,就在于樛木之曲,此为累。何止纠缠,其实已是守护。 谁说“草木无情”,樛之为木,葛之为草,就在此种依 靠。它们生生世世,似乎就此交结。可以葱茏,可以 永生。就在那南边的某处,它们彼此依托。这个时候, 你还会把“南有樛木”当作简单的交代?由此兴起 的源源不绝的内在情绪,又怎会只停留在“葛藟累之”中?《诗经》了不起之处正在这里,我们似乎第一次 由此看到万物有灵或万物可怜。草木尚且深情,我们怎可无情?
接下来两句“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你可以说 是前两句自然引出,亦可看作是此刻我们大家都想说 的,这即是共情。经典作品就有此种功效,未曾察觉, 你已深入其中,你们有共同的关切,共同的苦乐,而 不再只是诗人单方面所要兴叹问询的。乐,表快乐,或说是真正的;只,句中语助词,无实义;福履,履本 义为鞋子,可解为践行、到达,此处训禄,亦为福义;绥,本义为车中绳索,这里引申为安定、踏实。两句 合之即是:真正的君子,会像樛木般无私有为,会福 佑或守护他周围的一切。这两句充满期许,一反起篇 两句静态描绘或理想状态中可能会有的一厢情愿或自 不量力,而赋予行为主体某种主观意愿。你说是强调 担当的一方也好,整个句子,就突然灵动起来,仿佛一 切已在眼前,我们身处其中。所以即便之前有不堪重 负或理想尚未着落的惆怅与恍惚,此刻突然之间就乐 观振作起来,你说是诗人由此释然或真正找到人生的 意义或目的也罢。但我们的确就此打开另一个世界, 或我们终于超拔现实的困厄,到达精神的共振。“君子”在此刻,何止特指某人,更可能像一个悠远的梦,寄寓 我们对人类所有的期待与想象,他们不只存在于过去,更应像眼前樛葛般相依, 自然而久远。我们再看下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 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 福履成之。
这两章,显然是重章叠句,我们来看变的部分:由“累”到“荒”再到“萦”的转换,除了各章协韵 之外,应是强调依靠程度的加深。荒,掩盖,不只前 面的依靠,更是庇护;萦,旋绕,此旋绕看来已是浑 然一体,无法分割。而由“绥”的安定,到“将”的 扶助,再到“成”的成就,亦是一个安稳富足不断加 强的过程。结论:这样的人儿,才是真正的君子,值 得一生相托。显然,到此刻,整个篇章的意绪,已不 只是可托付,而是已托付,且浑然一体,不分你我。或者说,该篇就是在这样的一唱三叹中,不断强化他们彼此之间的连接,而在我们眼前,似乎已自然浮现 那如樛葛般不可分割的人儿。他们一如既往,共赴前 程,而我们,正在他们之中。这是如何的激动人心。我们的心到此刻怎能得不到安慰?这样的君子,如何 不值得期许?我们又如何不愿成为其中一员?这就 是诗歌所给予我们的美与力。我们如何能够不爱?
简单说,该篇借物起兴,以物作喻,物我和谐,同乐共荣。主要目的真是呼唤一种大公无私勇于担当的人格,或即他所谓的君子,而这才是整个社会前行、人民幸福的动力或希望。人们习惯上又把这篇看作是贺新郎,把樛葛相依比作男女共情,特别是主导男子一方,他值得依靠,可以托付。也许从它产生的 那天起,确实已具备此种功用。但今日的我们读之,显然不只此种意蕴。因为我们深深懂得,此种君子人格,此种造福他人不求回报,无论哪一种社会,哪一个时代, 哪一类人群, 都弥足珍贵,值得推许。
我们再来看《兔罝》: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
肃肃,兔网严密貌;兔罝,兔网;椓,敲打木桩;丁丁,敲打木头发出的声音;赳赳,器宇轩昂、威武有才貌;干,保护、护卫。该章起篇严肃,“肃肃”二字,何止正儿八经,简直是郑重其事:不是跟你开玩笑,哪怕打兔子埋桩这样的小事,我都会恭敬有序地做。“丁丁”二字,更是把此种声音渲染到极致,明明是敲打木桩声,偏有了上阵杀敌的意味。可以说,这起首两句诉之视觉听觉,极力铺陈夸张眼前所做之事,看那天罗地网般的兔网,听那敲打木桩的有力声音,其实是想说设置兔网的那个人,这样就自然引出后面的“赳赳武夫”。“赳赳”二字,何止响亮,应声而出的更是那位勇武之士:他是那样专业有力、锐不可当,像他这样的人,怎能不为公侯守卫城池?语气中满是自豪欢欣。似乎国家终于有望,国事终于有了交代。这种遣词造句,节奏声势,何止气象万千、波澜壮阔,简直一扫之前可能会有的羸弱或荒唐。这同样是《诗经》了不起之处,你以为它在拉家常,说闲话,云淡风轻中它已带你直上云霄。那种高峰体验,是真让你觉得一切想望尽皆实现,那身手不凡、壮志凌云的好汉就在眼前,或就是你自己。所以,后世把它当作好汉歌自吟曲不是没有道理。我们继续往下看:
肃肃兔罝, 施于中逵。赳赳武夫, 公侯好仇。
肃肃兔罝, 施于中林。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
这两章显然也是重章叠句,首句完全没有变化,就像《樛木》的歌咏中心就在“樛木”一般,这篇的歌咏中心显然也在“兔罝”。比之前面章节,我们看看“兔罝”之形象及功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之前我们还把它当物,当捕兔工具,那到后来,我们已把它当人,当作那位勇士。此种物我为一的写法再次让人惊叹。
我们接着看“施于中逵”“施于中林”又发生了 什么变化?或者说,我们来看这两句中的变与不变?施,延展、延伸,或者干脆是人为的设置,即把前面编织严密的捕兔工具“罝”设置在大路上,设置在树林中。逵,四通八达的路;林,树林,密林。可见真已天罗地网无处不在。哪里是捕兔子,即便敌人来犯,断无逃跑可能。如果说,上章的“椓之丁丁”还只是以声势逼人,摇旗呐喊,甚至虚张声势,那后面两章的“施”就不只是掷地有声,简直就是沙场点兵,排兵布阵,就不说后面“中逵”“中林”所到的场域,何止是豪气冲天,简直就是无处不在,无往不胜。或者说,此种声威,已涵盖所有可知领域。而这种写法,更是调动读者或观者所有情绪,达到现实不可及之境。那些过往的惆怅不安、现实的苦闷难耐、未来的可能战果,尽已托付眼前。何止好汉卫国,何尝不是我们年少时的梦:那样地孔武有力,那样地多谋善断。哪有他克服不了的困难,哪有他不能逾越的鸿沟。这是如何的乐观豪迈,这样的人,不只为公侯保卫城池,更可周行大道密室共议,做公侯的好伙伴、国家的守卫者。仇,同逑,配偶伙伴;腹心,心腹,亲信。由伙伴到亲信,自然是程度加深。可以说,最后两章的咏叹夸耀,不只顺理而然,更是水到渠成,谁能说好汉卫国不就是这个样子?
这篇传统解读,是咏猎人。起篇之“兔罝”,后人甚至以为是“虎罝”之误。好像打兔子无须这样正儿八经,这种写法或渲染简直是开玩笑。可狡兔尚且三窟,若不专业,如何能打着兔子?反之,若连打兔子这样的小事都可亲力亲为,全情投入,这样的男子如何能不值得信赖?况且,人家这种深谋远虑,精心布置,何尝不是儒家所谓的“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由此更可看到对他的个人期许。也就是说,诗人不只指望他是一个好的猎人,更指望他能保家卫国,成为国之栋梁。我们只能说,这种寄望,无论是妻子对丈夫、母亲对儿子,还是单单就是对一种男性力量与智慧的呼唤,都不为过,都不会过时。
当然,《诗经》作为先秦乐曲,首先应符合歌咏者的语言习惯,情意所指,就《兔罝》而言,“后妃之化”“南人归服”固然牵强,但看作自诩之语,或武士之歌,却颇足观。歌者即为武士自个,武士价值所系,为公为侯,其实就是为了国家。简单说,该篇最初召唤或赞美的也许真是保家卫国的武士。自然咏唱中所涵纳的是真实的情意与托付。 犹如《樛木》 篇中“樛”的独立与坚强,“葛”的缠绵与深情,《兔罝》篇中,我们同样看到武夫的有为,及公侯或国家的信任,某种层面上,这两者真是同生共荣。往大点说就是,国家乃至社会,既需樛木这样的君子,更需兔罝这样的武夫,也即君子可期与好汉卫国缺一不可。
如果说《樛木》让我们看到人格的宽广豪迈,于无言处,可为人师,可堪托付;那《兔罝》的孔武有力就让我们觉得声气相投,你说是自诩也罢。这两篇也不单是君子与武夫的悬置对比,是君子的自律,或武夫的修为,是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与对勇武之人的倚重,更是对文能兴邦、武能定国或就是对文韬武略的最初想象。虽然前一篇会多些虔敬,但并不存在真正的距离,而是实实在在地我愿成为你,让此福禄长存,终生相依。后一篇也不单单是咏国之栋梁,更是对好男儿实干家的个人期许,叠字叠词的应用,在表亲昵赞赏的同时,更意味着你我一体无时或离。
《樛木》就声音而言,比较内敛,或者说是没那么响亮,它冀望于人,应是内化,或就是后世儒家所推崇的自我修养。但《兔罝》给人的感觉明显不同,它甚至就是诉之于听觉。先不说那些叠词的堆砌,似乎任一个物事、动作,在他这里,都值得大张旗鼓地宣扬、歌颂、召唤、回应。根本不是“我”说了完事,而是你必须听到,必须践行,且心甘情愿。简单说,其声音之响亮,召唤之热情,类似于宣言、舞蹈,邀约你加入,或就是生命的律动,就在你的自我觉知中。突然在想,怎样的社会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怎 样的声音,才让人觉得声息相通?这应该就是后世所谓的“治世之音”,悠游从容,不只阳刚之气,更应是一个社会整体向上时才能发出的声音。在此层面上,它跟《樛木》就像二重唱,一个低音轻喃,作用自身,一个旁响外露,召唤他人,路径不同,方向一致,共同完成国人对君子人格与好汉卫国的最初想象。
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问题,所谓君子人格,武夫豪 情,究竟是哪个社会特有,还是后世儒家为其赋予?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一个正常的社会,必是对个人品格 操守有所规范,或者说,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是自然而然。对武夫行径的要求亦然,它不应是粗蛮的存在,而应恭谨有余,堪当大任。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勇猛向前,不忘任何小节。然而,后世对这二者的认知,似乎越来越割裂。文则肩不能挑,武就粗鲁莽撞。甚至直接出现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远庖厨,就不说打兔子。武夫可妄为,更别说顾细谨。而君子动口不动手,则成为劳心者的标配。打兔子这样的行为,又如何能提上桌面。我们甚至不知是人的意识发生变化,还是时代审美不允许这二者并存。但我们明明在不断提倡“知行合一”,这又何尝不是做人与做事的统一。我们现代人的立身处世,难道就不该以此为鉴?人格分裂怎就会成为我们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