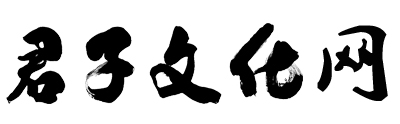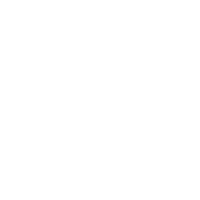“苏门六君子”散文的文统与风貌
阮忠 教授 海南师范大学
摘要:“苏门六君子”是北宋文坛很有意味的现象,他们遭际或同或异,无妨聚集苏轼门下,尚韩步苏,接受欧苏散文范式的影响,为文大体追求自然平易。从文体审视,其论说往往有家国之忧,求为世用而理明辞达;书信与序文以叙引论或论中兼有叙事,平和淡定;记文虽不乏好说理的特征,却因关乎人生,通脱超然,趣味各生。“苏门六君子”由此造就的散文风貌,尽管为苏轼的散文华章遮蔽,但在古代散文史上仍不乏自身的光彩。
在北宋欧阳修、苏轼古文的巨大魅力和影响下,宋文六大家中的王安石、曾巩及苏洵、苏辙四家古文成 就的光彩都被有所遮蔽。其实北宋散文的彬彬之盛是许多文人造就的,被遮蔽者众多,其中就有苏门文人。但他们作为文人群体在北宋文坛上有自身的地位,也为后人关注。
一、关于苏门文人
苏门文人,北宋晚年的翟汝文在《东坡远游赋》中感慨自己成人后苏轼已贬儋州,耳闻未能拜见。并说 当时“士无贤不肖皆曰东坡之门人”[1],这既在于苏轼的文学地位和名望,又在于苏轼好吸纳同道共趣的文人,与其说待他们如门人,不如说待他们像朋友。秦观在徐州拜见苏轼,临别有《别子瞻学士》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2]135 而苏轼在徐州任上,读了黄庭坚寄呈的古风二首,给黄庭坚写信称道他的诗“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 弃,与世疏阔者,亦莫得而友也”[3]1532。苏轼平等而有敬意地对待仰慕他的士人,故其门下士人芸芸。即使是身居贬谪地,从他问学而被视为他门人的也常见,如海南的姜唐佐、黎子云等。
杨胜宽梳理过苏门文人,据他不完全统计,“苏门文人集团应有50人左右”[4]546,“集团”中人,年龄与地域有很大差异,更宜称为不自觉形成的文人群体。王水照说:“‘苏门’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松散的文人群体。它经历了先由个别交游到‘元祐更化’时期聚集于苏轼门下的自然发展过程,形成以苏轼为核心,‘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不同层次的人才结构网络。”[5]其实,苏门文人在文学史上常为人称道的是“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四学士”为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后增加陈师道、李廌,则成“六君子”。前者因官职而名,后者因六人的道德品行的趋同。其后苏门文人群体还在扩展,又有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被称为“后苏门四学士”,但这四人的诗文多散佚,故讨论苏门文人往往集中在“苏门六君子”。他们是苏门文人群体的核心,也被人视为“苏门文人集团”。
“四学士”之名,最早见于《宋史·黄庭坚传》:“(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6]13110 而“六君子”之名,最早见于南宋王十朋的诗:“斯文韩欧苏,千载三大老。苏门六君子,如籍湜郊岛。大匠具明眼,一一经选考。岂曰文乎哉,盖深于斯道。”[7]他把“六君子”比作韩愈门下的张籍、皇甫湜、孟郊、贾岛,并说他们经苏轼遴选方入苏门。苏轼自己则说:“比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盖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3]1581他对此很自得,苏门文人中几无人能及“六君子”,只是没有道出“苏门六君子”。而苏门文人之文,还有“苏门后学之文”的提法,概念宽泛,好者往往着眼于“四学士”或“六君子”之后的文章,关注苏门的文学风气。
苏轼与“六君子”多有交往,诗词相为唱和、论诗论文论书法,元祐二年(1087)苏轼在京师入翰林,“六君子”聚于苏轼私宅,乐甚。其后,“四学士”又参加了在王诜家的西园雅集。书法家米芾兴起作画以纪其 事,“六君子”彼此之间也有交流,多见于他们的诗文。“苏门六君子”之文的成就难与“宋文六大家”相较,但他们都有相当多的散文写作。《全宋文》辑黄庭坚文63卷、秦观文19卷、晁补之文39卷、张耒文22卷、陈师道文9卷、李廌文4卷,其中各自除少量的辞赋和骈文,主体均为散文,因人而异,创作的状态并不均衡,但不妨碍对他们散文风貌的整体考察。
“苏门六君子”生于北宋仁宗居位之末,生活在北宋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时期。仁宗中前期的社会政 治开明与文化昌隆,在宋神宗即位后发生变化。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政派的熙宁变法,与范仲淹等人力主 的庆历新政之间萌生朋党之争,政坛的撕裂更加剧烈。新旧党争之下,苏轼在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中因政见 不一,站在王安石派的对立面,遭遇了乌台诗案,有了“旧党”的标签。元祐年间旧党以司马光为首一度复 盛,但进入绍圣后,朝廷重新清算旧党,苏轼被贬惠州、儋州。“六君子”,尤其是“四学士”与苏轼命运相系,均受牵连,流贬也在他们身上发生,陈师道、李廌不乐仕进,仕途自不辉煌。
“苏门六君子”在南宋就获得很高的赞誉。马东瑶说的后人以“君子”视之,尽管这更多的是道德评价而不是文章评价,但他们均不因道德为时所重。略略审视一下《宋史·文苑传六》同时收入的“苏门六君子”传。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学问文章,天成性得”[6]13110;仕途平平,因编《神宗实录》遭诬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流贬到宜州做编著,61岁时死在任上。有《黄庭坚全集》。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早年慷慨盛气,刚强正直。曾任太学博士、国史院编修等,因属旧党被贬杭州通判等职,后徙雷州,徽宗登基时遇赦,返京途中病死于藤州。有《淮海集》。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官著作郎、国子监教授等。因修神宗《实录》失实,降通判应天府,后坐党籍被贬,还居济州金乡东皋归来园,自号“归来子”,病逝于知泗州任上。有《鸡肋集》。
张耒(1054—1114),字文潜,楚州淮阴(今江苏淮阴)人,少聪颖能文,从苏辙学,曾任临淮主簿、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等职。坐党籍降职,又因为苏轼举哀,贬为房州别驾。晚年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有《张 耒集》。
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16岁以文章拜见曾巩,为曾巩赏识,后游学苏轼门下。曾任徐州、颍州教授,秘书省正字等职。一生无意仕途,晚年贫寒而死。有 《后山集》。
李廌(1059—1109),字方叔,号济南先生、太华逸民,华州(今陕西华县)人。早年携文拜见苏轼,却在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时落第。苏轼与范祖禹曾欲同荐李廌于朝,未几两人相继离京,不果。李廌再试仍不举,从此绝意仕进。有《济南集》。
马东瑶论述“六君子”与苏轼的文学之交,引用了张耒《明道杂志》中与苏轼谈诗的轶事。苏轼诗“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8],黄庭坚不平,说“白头”当改为“日头”,岂有用“白”对“天”的道理。张耒不以为然,苏轼对张耒说,如黄要改,也不奈他何。就此,马东瑶说“三个‘不’字具有象征性地体现出苏门文人集团在文学上的自立意识与自由辩论精神”[9],也可见苏轼对待门人的胸怀和开放态度。虽说“苏门四学士”和苏轼都上了元祐党人碑,但他们在政治上的相互支撑并不明显,无一人像欧阳修为范仲淹等人辩护一样,敢于痛斥高若讷司谏,并写《朋党论》公开论战。苏轼仕途跌宕,总还有官至礼部尚书的时候,而“苏门六君子”为官卑微,除黄庭坚、张耒年及花甲外,其他四人都在诗文创作力最旺盛时辞世,人生无奈和遗憾同在。
二、“六君子”以“尚韩”构成的文统
司马光元祐元年(1086)上《奏乞黄庭坚同校〈资治通鉴〉札子》,称黄庭坚好学能文,为世公认。好学正是黄庭坚以学问为诗的根本。黄庭坚力主文章不随人后,自成一家,致力于诗歌创作上“夺胎换骨”“点铁 成金”的理念和生新瘦硬风格的追求。关于散文,他在《答洪驹父书》其二里对外甥洪驹父直陈,说驹父的 文章写得尚好,但少了古人绳墨,劝他再熟读司马迁和韩愈的文章。韩愈兴古文,只读三代两汉之书,司马 迁之文在其中,并在《进学解》里点到了“太史所录”[10]910。欧阳修学韩愈之文,举进士之后与尹师鲁等人倡古文。韩愈有词必己出、文从字顺论。当尚韩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石介把古文风气引向险怪而形成“太学 体”的时候,略小于石介的欧阳修则在尚韩时引导“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11]1056-1057。他和石介为文取法的路径相同,但取法的风格不一。韩 愈为文重平易,为诗好奇崛,石介求新,为文“险怪”正是取了韩诗的奇崛,化韩诗之风为己之石文之风;而欧阳修承袭韩愈提出的儒学道统取了韩文的平易。欧阳修主张切中时病而不为空言,道胜文随,“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1]664。故苏洵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12]328-329这种散文风格正是从韩愈过来的,而他说的韩文行于世30年,且这30年后还有苏轼等人在延续,意味着“苏门六君子”之文是在这种风气中成长。张耒就说 过,当时“世之号能文章者,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13]844。
苏轼嘉祐二年(1057)科考得中之后照旧例写了《谢欧阳内翰书》,数说五代之后文教衰落,当今圣上(宋仁宗)澄源疏流,招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以复两汉三代之风。这正是韩愈的卫儒道倡古文之路,欧阳修的古文观与之契合,故欧阳修对苏轼大加赞赏,说后世人将只知道苏轼而不知道他欧阳修。然黄庭坚却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所谓的东坡文章短处在“好骂”,是他批评的锋芒和性情的真率表达。苏轼在《与二郎侄书》里是这样说的:“凡文字,少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14]意在文章的写作过程当从气象峥嵘绚烂归于平淡。人也在这一过程逐渐老去。
黄庭坚追求“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15]474。其所宗所趣,来自韩愈所说的三代两汉之文。他曾说:“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15]470这就是文章的开阖自然,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往年向苏轼请教文章作法,苏轼让他读《礼记·檀弓》,他读过百遍,然后一眼即明后世人作文章不及古人的毛病所在。所以他会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15]470。理得辞顺,要在自然,这与他在诗歌创作上化学问为诗的刻意求奇出新很不一样。在另一封给王观复的信中说:“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11]471因此,他批评建安以来的文章好作奇语,故气象衰疲,而“近世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秦少游,乃无此病耳”[15]471。他把秦观和欧、王、苏同论,在于秦文不好作奇。并在《答何静翁书》里称道何静翁,“论史事不随事许可,取明于己者而论古人,语约而意深。文章之法度,盖当如此”[15]464。语约意深也是他崇尚的基本手法与风格。
秦观少随苏轼学文,初“词采绚发,议论锋起”[3]936,与少年苏轼相似。后在《韩愈论》,说先王之时,士 大夫无意为文。周衰以来,好文者接踵纷起、各自名家,总而论之,无人可及韩愈者也。理由在于文章四体 说理、论事、托词、成体,前之作者没谁能及韩愈四体皆备,后之作者则没有谁超越韩愈。他断言“杜氏、韩 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2]752。他这里对韩愈的推崇,和黄庭坚有同一的立场,黄庭坚说过:“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15]475不仅如此,秦观还在言及叙事之文 时,点明“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作是也”[3]751。不虚 美不隐恶的实录,是班固对司马迁撰述《史记》的评价,如是撰史追求写作的真实,秦观认同这一点,并和黄 庭坚一样,也是受司马迁、韩愈之文的深刻影响。不仅黄、秦,还有张耒,他曾对曾巩说:“自三代以来,最喜读太史公、韩退之之文。”[13]844 司马迁奇迈慷慨,但“文章疏荡明白,简朴而驰骋”;韩愈之文如先王衣冠、郊庙鼎俎,却“放逸超卓,不可心揽”。韩愈之后有欧阳修出于孟轲、韩愈之间,“积习而益高,淬濯而益新”,曾巩之文则出欧文之门,“文章论议,与之上下”[13]844-845 这番话表明了张耒文章的基本取向。他还在《答李推官书》里以水喻文,但不类苏轼《自评文》里以流水自喻文章的气势与自然,而是说水顺道而决,因适生变,关键是“理”在,“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13]829。他以此比喻说理与文的关系,视文为寓理之具,理胜文则文不期于工而自工,故“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13]829。而这理又与文相应,当发于自然,甚至说“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这一点与他在《贺方回乐府序》中说的“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13]755相合,为文重在发乎性情的自由而自然的表达。然为文之道,是南梁刘勰说的“人之禀 才,迟速异分”[16],不宜喜速而鄙迟。
张耒作《晁太史补之墓志铭》,说晁补之少时为文,上追《左传》《国策》等,下尚韩愈、柳宗元之文;而陈师道《答江端礼书》论文:“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约之以义,行之以信,近则致其用,远则致其传,文之质也。大以为小,小以为大,简而不约,盈而不余,文之用也。正心完气,广之以学,斯至矣。”这与他以拙朴论文相近,文之质,要在述志;文之用,要在简约。又说:“学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17]320学与思相通,终归于理;志与气互融,实现于文。这在理论上都有韩愈思想的影子。
所有这些,虽达不到苏轼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的滔滔汩汩、行止自如之文的境界,但从司马迁、韩 愈、欧阳修、苏轼相沿而下,欧阳修效韩愈,擢拔苏轼为进士后感慨,要避开一条路让苏轼出人头地,希望苏轼也继承韩愈的古文传统。苏轼对欧阳修说“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4]1424,也是一片真心。苏轼晚年对张耒说:“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 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4]1427 这样的“古人”关联,既为道统,也为文统,导致苏门文人彼此趣味相投,故散文有走向平易的一致性。黄庭坚不主张为文之“骂”,不尚情绪激越,不重怨愤刺讥而务平和。陈师 道就苏轼诗说了一句类似的话:苏诗始学中唐刘禹锡,故多怨刺,学当谨慎。况且陈师道诗歌创作上追 求的“宁拙毋巧,宁朴无华”[4]311 必然会影响到他文章的拙朴。苏轼的“好骂”在韩愈、欧阳修也曾如此。他早年为文的“峥嵘”,这是韩愈尚孟的结果。因之形成的文统经欧阳修到苏轼,苏轼“盖尝自谓学出于孟 子”[18]26,与韩愈相应,最终又可从司马迁上溯到孟氏的平易和畅,“六君子”亦然,尚韩文,自觉置于欧苏散 文的范式之下。至于奇,则是张耒说的“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13]826,说透了,这奇实为自然。
三、论说理明辞达蕴含的社会忧思
散文入唐以后,因用生体的现象造就了文体繁多。宋人承袭,“苏门六君子”亦在其中。他们的散文受 欧、苏的影响,学欧文的条达疏畅,取苏文的随物赋形,趣味相投,文风趋同。“六君子”在北宋中晚期命运不济,揣家国之忧而有社会关怀之情,因之而生时论。黄庭坚的时论甚少,他有《策论》其一道“圣上览观六经之治,哀元元之不逮,爰诏儒臣,典领删次,务以合古便今,可谓至德”[15]1558,认为《六经》是致治的成法,以此求仁义兴而百姓安。
秦观少时像晚唐杜牧,强志盛气、好大见奇,喜读兵书,以为功誉可力致,故常虑天下之事,也导致他在 仕途所持的积极态势。他还说自己:“淮海小臣,不闻庙堂之议、帷幄之谋,独耳剽目采,颇知当世利病之所 以然者。”[2]493所以他在元佑五年(1090)上《进策》30篇言治国方略。《国论》说舜治秦道,劝哲宗德治天下;《主术》说人主之术在任用善于政事之臣、敢谏之士,不然弊坏精神、竭尽精力也无益;《治势》则说治天下当 审势,逢强用宽,遇弱使猛。他对时政充满忧思,如说“嘉佑之后,习安玩治,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 臣以苟简自便”[2]517。元丰之后,执事者矫枉过直,“上下迫胁,民不堪命”[2]517,因此主张中和以成自然缓势 以安天下。秦观这些策论纵横捭阖,忧心深重,理直气竭。元佑二年(1087)朝廷党争又起时,他写了《朋党 论》上下篇。
北宋王馬偶继晚唐李德裕之后作《朋党论》,说朋党的辨识之方;欧阳修作《朋党论》说君子有朋、小人无朋,人君当用君子之朋图天下大治;苏轼步欧阳修之论作《续朋党论》,援古证理,借春秋、李唐之朋党,说人君当力戒如同恶草、不种而生、去之复蕃的小人朋党。秦观相沿,作《朋党论》说君子、小人朋党在所难免,人君务辩奸邪。他在上篇引述《易》之阴阳、尧之八元、八凯、四凶、东汉三君、八顾、八俊等唐之牛李党争之事,说人君不辨朋党,终致小人得志,君子受祸。并在下篇说当朝之事,言及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为小人,以“朋党”之名构陷,遭致罢官流贬,劝哲宗道:观《易》道消长之理,稽帝虞废举之事,鉴汉唐审听之失,法仁祖察见之明,杜媒蘖之端,窒中伤之隙,求贤益急,用贤益坚,使奸邪情沮而无所售其谋,谗佞气索而无所启其口。则今之所谓党人者,后世必为元老大儒社稷之臣矣。[2]547秦观由史及今,其论是继欧阳修之后为韩、范等人论辩的延续。他用铺排说理,强化了论辩的力度,以质实 切用,不似苏文的从容,而有欧文的激昂以纠时弊。与《进策》相辅,他还有论体和说体之文,如《变化论》 《君子终日乾乾论》,彰显了自己细密思致和军国大略,欲求用于今,实沦为空谈;说体之文,如《心说》《十二经相合义说》等,论理却落于玄妙。
张耒少苦贫贱,13岁能文,17岁丧亲,后为官于州县,穷愁困塞不可胜言。形于文章,则舒己情怀,自慰寂寞。虽然他推崇满心而发,肆口即成之文,但他重文章之理,散文亦多好议论,不得志时无碍有深刻的治国理政之思。如说“法度之弊,起于德不足而求胜其民,而败于启民之邪心而多怨”[12]578;“夫刑戮赏赐,非不足以立畏爱也,使必陈其物,设其具,则刀具金帛亦不给矣”[13]583。诸如此类,还有《法制论》《悯刑论》《礼论》《敦俗论》等,关乎社会治理,系统深入,理明辞达。
晁补之散文的文体众多,他的55篇策问是试士的设问,有问待答。当是他中了进士授北京国子监教授、太学正后的事。虽说这些策问在晁补之文中有问无答,但可以看到他在《亳州谢到任表》自称粗知学问 的所指。这些学问涉及儒、道、法、兵等诸家之学,重在议论说理,如《礼乐》《兵法》《老子》《赏罚》《祭祀》《屯田》等,可见取士重学,意在经世。如《吏部》问“由汉以来,此职寝重,其间能以鉴裁清白名一时,谁者为盛?
幸条其说,以备上之采焉”[18]213;《用威爱之道》问“将求先王所以用威爱之道,宜必有说也”[18]218。这些文字在晁补之散文中别具一格,而他时政论的襟怀、韬略、决断、雄辩所展示的风采,主要在《上皇帝论北事 书》《上皇帝安南罪言》以及《七述》里。《七述》是他19岁在杭州拜会苏轼畅谈杭州的秀丽富饶,提到枚乘《七发》、曹植《七启》,故退而有作以之献给苏轼,只是《七述》应归于七体之赋,自当别论。
陈师道的时论有《正统论》《取守论》《商君论》等,其自有己见,规模与系统均不及秦观,他曾对李端叔(之仪)说:“秦观之文,过仆数等。”[17]281并非自谦之词。他以儒学为正统,以仁义为守天下之具,以及斥责商鞅为历史罪人,都与苏轼思想相承。
与时政论相关,“六君子”之文还有两个走向,一为论兵,二为论史。
就论兵言,好读兵书的秦观论兵,如《奇兵》说:“万物莫不有奇,用兵亦然:兵之道莫难于用奇,莫巧于用奇,莫妙于用奇。……用奇之法,必以正兵为主,无正兵为主而出者,谓之孤军。孤军胜败,未可知也。”[2]614-615并以西汉霍去病之胜与李陵之败为例加以说明,这当是《孙子兵法·势篇》说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19]的阐发。他策论重说理,论理往往引经史为据,由古及今,重在对当下社会治国用兵之道的改造,用心良苦。
李薦以苏轼的文章为准的,“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辩而中理”[6]13117,因此形成的滔汩之势有苏轼文章风范。李之仪曾说李薦之文“如大川东往,昼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20],如李薦《慎兵论》说不宜用兵:
人君当视人犹己,以己推人,则好战之心自平。夫士卒之痛,思己之痛;士卒之伤,思己之伤。矢石在前,白刃在左右,法令在后,万死之间,幸于一生,其危心如何?彼贵贱虽异位,而喜惧好恶 之心无二,况复杀乎?[21]160
他还在《将材论》说当今选将:“今天下为家,四海为畿,罔匪臣仆,英雄尽入于彀中,多士咸在,众技自献,唯 君王所择。所谓能称筑坛告庙之礼,能胜推毂授钺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选而已。”[21]163 如是之论,体志 气韵俱备,气势充沛畅达。他说兵将,并不希望有战争,故在《将心论》批评战争的残酷,主张以仁政为重,孝治为先,宜治心以戒杀。
就论史言,秦观的策论中有历史人物论,如《晁错论》说斩了晁错,理直师壮,方能破七国用兵;《李陵 论》说他率五千兵士入匈奴是用兵的变道,不知行小变则不失大常,即孤军单进时,宜有大军相随为后援,李陵无大军相随,故败。治当世之事,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秦观自认为有经纬世事之才,却无用于 世。张耒则在《秦论》说秦亡非贾谊说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是民心本不向秦;《吴起论》说吴起 之败在于明法审令而不知与化推移当有的应时而变。他还有一系列的唐史论,如《唐论》上中下。他己见 独运,率性表达,正是典型的苏门风格。晁补之的杂论涉春秋、西汉、唐、五代史,就史书所载发论,如《楚不 能与晋争》,取《左传·襄公九年》楚子囊说“今吾不能与晋争”说道: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孟子以谓“乌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盖贵老敬长,所以训孝弟,而贤能所在,不必长老。是以晋政类能,少者位上,群臣乐推,强国罢争,才之所在,不系乎年也。[18]245
他把楚不能与晋争的原因挑明了,“贤能所在,不必长老”,不受“达尊三”的局限,说理简明平易。又如《陆贾交欢平勃》说西汉初年陆贾和陈平、周勃事,陈平、周勃平诸吕而定刘氏,得陆贾之助,“贾一言而两人成谋,社稷之计出其掌握,去产、禄如苋陆之易,措刘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岂不信哉”[18]263。不过,他的史论新锐而有见地的不多。
上述这些论说,暗透着他们对北宋末年国势走弱的深忧,论兵求实用,论史图借鉴,然均为不时用。苏 轼曾说秦观是“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3]1756,他希望秦观获得的是前者,可秦观不为世用享有了后者。就求用言,这也是苏门其他君子的悲哀。至于以论著晓后人,并非他们当时的意愿。
四、书序平和淡定蕴含的人文关怀
“苏门六君子”为文少不了说人生,当他们的社会关怀转化为人生关怀的时候,在书序之文中涉及自我或他人,仍然少不了议论。相对于时论,更容易在其中蕴含自我的情怀。
书信是古代文人因生活与交往常用的文体,黄庭坚给苏轼写信说:“庭坚齿少且贱,又不肖,无一可以事君子,故常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而终不得备使令于前后。”[11]457这是他最初对苏轼的真情表白,崇敬与战兢同在。苏轼死后,他给苏辙的信中说:“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谓遂至于此。何胜殄瘁之悲。”[15]460黄庭坚最初写信给苏轼是神宗元丰元年(1078),而他写给苏辙的信在徽宗建中 靖国元年(1101),前后20余年,黄庭坚视苏轼亦师亦友,情感如一。又如《与胡少汲书》说:“治病之方,当深求蝉蜕,照破死生之根,则忧畏淫怒,无处安脚,病既无根,枝叶安能为害?”[15]477 面临死亡,没有大悲;面临疾苦,没有大忧。
秦观给苏轼的信四通。苏轼在徐州建黄楼,嘱秦观作黄楼赋,赋成秦观有信说:“比缘杜门多暇,念嘉 命不可以虚辱,辄冒不韪,撰成缮写呈上。词意芜迫,无足观览,比之途歌野语,解颜一笑可也。又多不详被水时事,恐有谬误并太鄙恶处,皆望就垂改窜,庶几观者不至诋诃,以重门下之辱。”[2]986-987他是苏门中人,说这事多谦,文风平和,但在《与孙莘老学士简》说苏轼贬黄州事,“苏黄州……在黄甚能自处,了不以迁谪介意,日但杜门蔬食,诵经读书而已。昔之论者常患其才高太锐,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2]998。苏轼在黄州曾有缥缈孤鸿、人生如梦的不平之叹,但他在这里平静地说苏轼的黄州生活,即使是给苏辙的信里说自己生性与世异驰,似乎会有愤激之声,然说出的却是遭摈弃乃理之当然[2]1002。
张耒有《投知己书》,说到古之文章之作十之八九出自失意之人,虽然事物百态,不免长歌恸哭,诟骂怨 怒,但他的书信体散文如《上文潞公献所著诗书》论诗人情志、《上曾子固龙图书》论君子文章,都中正平和,诗之出乎人的私意却能感动鬼神,惟至诚方能如此;文章之刚柔缓急、繁简舒敏,都出于至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浮于心,也不浮于德。至诚是他重要的思想观念,在《上唐运判书》里说到三代社会,公卿大 夫待下仁爱忠厚,乃在于至诚;然三代之下,不再有至诚之心,故无爱天下大众之心。他这样说着普泛的创 作与治理社会的道理,语气的平和却不失事理的深厚。
晁补之也有写给苏轼的《上苏公书》《再见苏公书》,他说苏轼“胸中千变万态,不可殚极。而要萦纡由折,卒贯于理,然后知阁下所之为自许者,不诬也”[18]29。所谓苏轼“卒贯于理”之“理”,是宋文也是苏文的基本精神,晁补之的书体文较之黄、秦、张的气势要大,总不脱理也是自然的归宿。他在《上杭州教官吕穆 仲书》数说三代以来的社会进程的成与败,及宋则道:“国家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两汉 之余,而复三代之故。焦心以问治,降意以下贤,而士之怀瑾握瑜者,纷纷藉藉,云翔蜂起,奔走自效,不待招来。”[18]31他这番话为王朝唱颂歌,重心是陛下招贤天下响应,以致天下已无隐士,万一有也是无能之人。然后说自己不自弃而求有用于世,并向吕穆仲表示,愿受教于他的门下。然而他在《谢外舅兵部杜侍郎书》里说了另一种情形:“补之于苏公为门下士,无所复赞。然刚洁寡欲,奉己至俭菲,而以身任官责,嫉邪爱 物,知无不为。尤是不忽细务,其有所不复旦尽,视去官职如土芥。”[18]33在求官与去官之时,他的表达都给人平和的感觉。
陈师道给苏轼、秦观、黄庭坚、张耒等人写信,叙说自己的生活状况和人生认知,如在《与黄鲁直书》其三里谈及自己:“某素有脾疾,近复暴得风眩,时时间作,亦有并作时,极以为苦,若不饥死寒死,亦当疾死。然人生要须死,宁校长短?但恨与释氏未有厚缘,少假数年,积修香火,亦不恨矣。”[17]298 陈师道家境不好,生活贫寒,他告诉黄庭坚,近来脾疾与眩疾并发,面临死亡说出“宁校长短”,是韩愈《落齿》说过的“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10]126。而所谓人生与释氏缘分不厚的遗憾,似乎有生死难以轮回之慨。他在给苏轼的 《上苏公书》里说君子之于事,当以本位为限,劝苏轼居其位则尽己言,不必越位极论。其中言及离别:
士方少时,未来之日长,视天下事意颇轻之,亦易为别。至其迟暮,数更离合,又以为难。此盖志与年衰,顾影惜日,畏死而然尔。谢太傅尝谓中年以来,一与亲友别,数日作恶。谢公,江海之士,违世绝俗乃其常耳,顾以别为难者,岂酣于富贵而习于违顺也耶! 由是观之,以别为难,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当以老为戒,以富贵为畏耳。[17]294
他说与苏轼相聚而再别之事,较之少年离别与老年离别,想到的是光阴倏忽,死之将至,别之难实因重逢也 难。陈师道用家常话讲述这些道理,同样体现出宋文好议论及自欧、苏以来尚平易的特点,他就此传达自己的深刻之思,给人启迪。
再说序体之文,这里有张耒的赠序如《送李端叔赴定州序》《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等,说昔日交往,道当下别情;晁补之的名字序,如《从兄字伯顺序》《李浩字季良甫序》等,借名字生论,阐发学理,纵论古 今。这里主要说“六君子”的文集序。他们文集序甚多,黄庭坚为王安石之孙王定国文集作序,又为晏殊 之子晏几道作《小山集序》,且在词坛深具影响。这篇序多说晏几道的人生,其中说他痴绝于人的“四痴”,素为人道: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 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15]413 这番话对晏几道一生作了很好的勾勒,他的“痴”是性情的极致,不阿谀不媚俗,却又显得天真和豪纵。说 到词,黄庭坚因晏几道而说自己:“予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非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邪?”[15]413他以晏几道词为自己辩,较之书信之文,语言更为活脱。
秦观亦然,但他在比拟中有灵动的叙议,如“木不能飞空,托泰山则干青云;人不能蹈水,附楼航则绝大海”[2]1255,意旧辞新,让人产生联想。又如《逆旅集序》记叙有人说言欲纯事,书欲纯理,批评他为文驳杂不纯,儒佛道、医卜鬼神都在其间,他笑而辩言:
鸟栖不择山林,唯其木而已;鱼游不择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计事而处,简物而言,窃窃然去彼取此者,缙绅先生之事也。仆,野人也,拥肿是师,懈怠是习,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偶有所闻,则随而记之耳。又安知其纯与驳耶?[2]1258
秦观除坐而论道外,也有这样“随而记之”的率性文字,这与苏轼的杂文风格相似,行所欲行。张耒说他一 生作文不多,但一一精好可传。
李薦有《陈省副文集后序》说人生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居其一可无愧于后世。立言之言,形于 文章,他主张言必有义,字必有法;文须有体、志、气、韵:无体不成文,无志无所用,无气憔悴无生意,无韵神 色昏蒙,四者全方为文章的理想境界,如说陈省副文气萧散简远,即知其有洪人之量;文之理方则有正直不 回之忠;文之意渊淡冲粹,即知其有中和无邪之德。这是从文看人;反之从人看文,则是“正直之人,其文敬 以则;邪谀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21]125。人品与文品的评说,终归还是知人论世,图真务实尽在其中。作为苏门弟子,李薦说“先生文章忠义为当世准的”[21]135,并在《程因伯诗序》里为先生辩:斥责他的同乡才德、名望、功实均不及苏轼却损抑苏轼,如螳螂拒轮、蚍蜉撼树,不度德量力。这在“苏门六君子”中算是激烈的文字,然后他仍然归于平和,称道程因伯以诗为贽不贪富贵而求为贤人之徒。与之相应,他的《圣 学论》论力主崇经尚仁,明言不与迂儒、佞儒共学,表达朝廷当“妙选忠义正直、博学守道之士,以备顾问,则用力少而见功多,适道正而为利溥”[21]159。他承袭苏轼的思想,也为苏轼辩,希望苏轼为朝廷所用。“苏门六君子”地位卑微,其书信与序文各自不同的表达,多是遭际不一,所感有异,以叙引论或论中兼事,平和淡定,也是为文平易本身的自然品格。
五、记文通脱超然寄寓的多元趣味
黄庭坚说:“读书须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不虚用功。”[11]485他曾说王观复下笔 不凡,但读书太少。而他自己因博学而为诗文,常有意在诗文中彰显学问,如《松菊亭记》说:“期于名者入 朝,期于利者适市,期于道者何之哉?反诸身而已。”[15]438“反诸身”说,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的“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22]。自然导入文中的韩渐正享有富贵之后,筑堂于山川,伴松菊以就闲。又如《黔南道中行记》说他夜宿黄牛峡,想起欧阳修的诗和苏轼记丁元珍梦中 事;因泉水清冽说陆羽《茶经》记黄牛峡茶可饮,令舟人求之。这样一些旧理往事,耐人寻味,启人多思。黄 庭坚这样在记文中重学问而显庄肃的只是一种风格,同为“六君子”,最少不了的是以议论见理。黄庭坚如 此,其他五人也如此。
如晁补之的《近智斋记》就近智斋发论,说好学近智勉人;《睡乡阁记》说齐州政淳俗和、安恬舒适,太平犹睡乡。继而说尧舜无为之治后,睡乡渐失,战国、秦汉之际,“悲秋伤生,内穷于长夜之饮,外累于攻战之具,于是睡乡始丘墟矣”[23]45处士慕庄周,乐而忘归。而他反省过往,自感迂腐,欲因斯人而问津。至此,晁补之对北宋晚年的失望与悲情尽显。他还叙柳宗元居永州冉溪而以己因愚触罪,更其名为愚溪,并在《愚溪对》里借溪神现梦,称己非愚,而是甚清且美,进而说自己在汶水之北、庐泉之上,取“清美”名己堂,故有《清美堂记》。
熙宁七年(1074)陈师道在金州,受命于开封刘刺为“忘归亭”作记,他先叙忘归亭下悍蛇鸷兽、狐鸣鸟声、暄寒雾雨、疾疢易作,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人凄然兴叹,怅然怀归。然登亭之后,则是另一种景观:于是相与登斯亭以向坐,则又志意舒徐,气血和平,蘧然而笑,栩然而歌,超然而忘归。其山川之美,临观之乐,不言可知,言不能尽也。士大夫去坟墓,背田庐,捐宗姻友旧,从事于异域,故虽君子无厌苦之志而有归心。居官有守,义不得去,念岁月之永而忧不可极,作为斯亭,与人同乐,以居而忘怀,其志壮哉。[17]362-363
怀归是人之常情,厌苦与否都会思乡念亲而有归心。但登亭有相谈时志意舒徐及眺望山川美色之乐,顿失 先期的忧惧而生忘归之心,陈师道款款道来,言说美景与心志契合的愉悦。又如他的《思亭记》说:“余以谓 目之所视而思从之,视干戈则思斗,视刀锯则思惧,视庙社则思敬,视第家则思安。夫人存好恶喜惧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23]366从这些常理出发,他说徐富家墓地之室可题为“思亭”,以便睹物思亲。这些记 文以议代叙,削弱了纯议论的枯燥。其《思白堂记》《二亭记》《披云楼记》也是如此。在这些记文中,他常自 生波澜,言事或论理蜿蜒曲致,情理兼胜。
李薦的记文相对于时论和缓得多,也少了苏轼同类文章的潇洒风姿。他的《安老堂记》说居士耻于附 炎趋势,安老于山林;《斑衣寮记》说天下之患,患在有求,“无求则无得失,无得失则无欣戚,无欣戚则泰然而乐全”[21]187,如是的从容淡定,彰显的是论兵、论将之外的另一种脱俗人生。他的《合翠亭记》与陈师道的《忘归亭记》有点相类,其中写道:
故将军杨氏之僧居其北冈,乔林蓊郁,蔽亏云霄,望之若不可通迹以登也。乃于杂花香草中得微径,委蛇绕冈址以登,遂于冈之巅得高亭,在乔林蓊郁中,无复见日,惟苍桧樛枝,翳靡纷披,使人忘怀远想,如在邃谷之岩上,左右烟壑,浓翠皆合,不复知为市朝人也。艰难登顶而居亭上,乔林苍桧、烟云缭绕,飘然若仙,忘怀自己为市朝人,远想随之也无。李廌状景粗放,却有优雅文辞与朦胧诗意。“六君子”的记文多议论之外,也有描写与对话,好议论的晁补之还善记叙描写,如《新城游北山记》记游,说新城(今浙江富阳)北山之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伏见堕石井,锵然而鸣。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鸟,黑如鸲鹆,赤冠长喙,俯而啄,磔然有声”。[23]26这宛如一幅大松图,松劲泉鸣、藤之蜿蜒、鸟之啄声,各具风采。登顶僧人相迎,转而再叙山顶之屋的景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23]26,于是有不知身处何境之叹。况时维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23]26-27。晁补之这样的游记虽少,但声色相合、动静互衬、轻游重景、因物及人的写法在同类的游记中少见。而张耒的《鸿轩记》 则用赋体的主客问答:
鸿轩者,张子读书舍也。客有言曰:“吾闻之,时其往来,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飞远举,能使弋人无慕者,鸿也。今子以戆暗不见事,几得谴辱于圣世,蒙垢忍耻于泥途,苟升斗以自养,而欲自比于鸿,不亦愧乎?”张子曰:“子之言是也。基予居此以己卯之秋,其迁也庚辰之春,与夫嗸嗸陂泽中猎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无类乎?“客曰:“唯。”[13]767
这有扬雄作《解嘲》、韩愈作《进学解》以自嘲的意味,以鸿自比,不合于俗而超然世俗之外。这较之议论,更显通脱超然。
记文中还有传记值得一提。如秦观用司马迁的史笔,写了一些人物传记,如《陈偕传》《眇倡传》《清和先生传》等。《眇倡传》为一眼失明的吴倡立传,吴倡家贫无以为生,与母西游京师,人或说在京城两目全者尚难自售,何况“眇一目”者。吴倡不以为然,至京师舍于滨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从数骑出河上,见而悦之。为解鞍留饮燕,终日而去。明日复来,因大嬖,取置别第中。谢绝姻党,身执爨以奉之。倡饭,少年亦饭;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嗫嚅伺候,曲得 其意,唯恐或不当也。有书生嘲之曰:“间者缺然不见,意有奇遇,乃从相矢者处乎?”少年忿曰:“ 自余得若人,还视世之女子,无不余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为!”[2]822-823
秦观实录以见少年之宠吴倡,是人间奇事,爱之所在,不在目眇。犹庄子说的美者自美,我不以为美;恶者 自恶,我不以为恶。实录之下,朴实自然,与人物传记相类,则有行状,如《徐君主簿行状》《鲜于子骏行状》等,这些文章与他的策论风格迥异。张耒也有一些传记,特殊的是他为诗作传如《嵩高传》《文王传》等,用于说理而非记叙,但有写实的《任青传》,寓言性的《竹夫人传》《书小山》,简朴平易,率性通脱。如《竹夫人传》: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川,往往散居南山中,后见灭于匠氏。武帝时,因缘得食上林中,以高节闻。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宫,自卫皇后以下,后宫美人千余人从。上谓皇后等曰:“吾非不爱若等,顾无以益我,思得疏通而善良,有节而不隐者亲焉。”于是皇后等谢曰:“妾得与陛下亲,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风陛下,罪万死。”于是共荐竹氏,上使将作大匠铦拜竹氏职为夫人。[13]799
他以竹为“竹夫人”,讲述的是竹夫人先宠后衰,张耒将她与班婕妤相比,却让她读班婕妤的《纨扇诗》而有两人同类的感慨,最后遭焚于未央宫。这个故事似乎在讲一个人悲剧,既像班婕妤,又像陈皇后;似乎又不 是说一个的人悲剧,而是正在衰落的北宋挽歌,他死后,北宋只过了12年就灭亡了。在他的诙谐里,饱含了心酸的泪水。
“苏门六君子”之文还有疏表启奏、颂祭碑铭等,不过他们主要的散文风格见于上,这些散文虽各有个性,但在群体风格上也多有共通之处,作为欧苏之文或说北宋六大家之文的尾声,其气度与风神难与前辈相较,好在他们文多坦然,光彩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