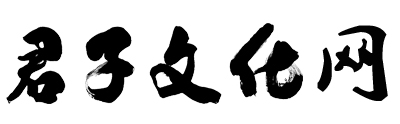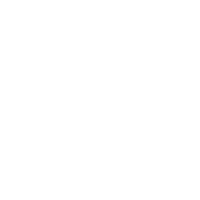从“君子不器”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基于知识与德性关系的辨析
叶 晴 清华大学
孔子不仅是思想家,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教育家。《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的言行,能为我们探究孔子的教育思想提供可靠的依据。要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不仅要把握其论述教育的具体方法、内容,更要把握其教育思想的目的指向和根本内核。与一般教授学生具体知识和实用技能的老师不同,孔子的教育旨在促进学生的道德修养,使学生成为有德的君子。后世儒家也一直把德性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这对中国古典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重新回到孔子教育思想的德性传统,能够使我们从古典教育中获取有益于当代中国教育的思想资源,为我们反思当代教育提供借鉴。
“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政》,而对什么是“器”,为什么君子不能成为“器”,君子应当成为什么等种种问题,孔子并未给出明确的解答。由于“道”“器”两个概念在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形而上意味,以及“君子不器”这一表述本身的思辨特征,这成为了孔子教育思想中最具有理想色彩和
开放性的观点,一直备受历代《论语》研究者关注。学者对于此章有不同的解释倾向;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此章是孔子在论技艺的单一化和多样化的区别,由此可引申出教育的专业化和通识化问题,得出孔子所主张的乃是一种非专业化的通识教育的结论。依这种观点,则学习专业分科的学生都只是“器”,只有经过“通识教育”的学生才是君子。这固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未能把握孔子此言的真正意味,而本章透显的应是孔子对德性教化和君子人格培养的重视。
基于此,有必要在辨析历代注家诠解的基础上,结合《论语》中孔子论器的其他章节,探究孔子“君子不器”所表达的真正意涵。此外,也要把此章放在孔子论教育和论君子人格的整体思想脉络中,结合《论语》其他篇章,以在整体视域中追求对本章要旨的准确把握。“君子不器”实际上蕴含了孔子思想中知识和德性的深刻辩证关系,体现了儒家德性教育的核心宗旨,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当代教育的问题,思考更好教育的可能方向。
收稿日期:202307 29
作者简介:叶晴(1998),女,广东韶关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202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儒家伦理学、中西比较哲学。
一、“君子不器”之诠解
在辨析各家注解的基础上,本节首先结合孔子在《论语》中论“器”的语境分析“不器”表达的 意思。对《论语》中“器”这一概念的全面分析,有助于理解孔子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如何使用“器”这一概念的。会通文意能够对此章形成更加合意 的理解,避免离文说意的诠释偏差,使得对“君子 不器”的解读是在尊重语义、还原文本原意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历代诠解
“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政》第十二章“子 曰:‘君子不器。’”[1]57对此章的理解,“器”是重 点。《说文解字》解“器”为:“器,皿也。象器之 口,犬所以守之。”[2]453“器”原本的意思是有一定 功能和用途的有形的具体事物,即器具、器物。《易·系辞上》则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3]736把“器”作为一个与形而上之道对立的哲学范畴,指现实经验层面的具体事物,这是“器”之本义的抽象化,指向与本体对立的“用”。从这两处大体可以看到,“器”的本义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功能,二是有形的具体用具。
再回到“君子不器”,历代对此句有不同的注解,这些注解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此章在讲一能与多能之别,强调君子应该成为融通多种技能的通才。如何晏引包咸解释此句:“包曰:器者各周于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4]96皇侃疏曰:“此章明君子之人,不系守一业也。器者,给用之物也,犹如舟可泛于海,不可登山;车可陆行,不可济海。君子当才业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5]33又如近代钱穆解:
器,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今之所谓 专家之学者近之。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后人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才艺。”才艺 各有专用,器,俗称器量,器量大则可以 多受,识见高则可以远视,其用不限于一 材一艺。近代科学日兴,分工愈细,专家 之用益显,而通才之需亦因以益亟。通瞻全局,领导群伦,尤以不器之君子为贵。此章所言,仍是一种通义,不以时代 古今而变……一个君子不像一件器具,只供某一种特定的使用。[6]38
包咸、皇侃等都认为此处是强调一能和多能之别,即君子不应该只有某一种才能,而应该成为一个博学多才、融通各种器用的完人。这一解释引起的是关于“通才”和“专才”的讨论,在钱穆的解释中也倾向于强调这一点。钱穆于其时代立场上主张君子不应仅仅追求成为“专家”,而应打破现代教育分工的限制,成为“通才”。
这一类的解释,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对于“器之量”大小的讨论。依钱穆,器量小则限于一才一艺;器量大则能够有多种技能,融通才艺,成为通才。则“器”和“不器”转向了“器”之大小之别,以一种定量的标准去衡定专才与通才,并以此为君子的标准,认为孔子不主张专业化的教育。杨伯峻也认为此章是说:“古代知识范围狭窄,孔子认为应该无所不通。”[7]14这就把此章引向了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矛盾,依此,就只有接受了通识教育,有多种才能的才是君子,那些进行专业学习的人则不可以成为君子。
第二类解释强调君子之能相通各用,是因为其首先是有德之人,有德乃可以至于通达,这强调了修德的重要性。如朱熹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材一艺而已。”[1]57刘宝楠解释为:“此则学为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故知所本,则由明明德以及亲民,由诚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国、平天下。措则正,施则行,复奚役役于一才一艺为哉?”[8]56这一类解释强调君子之“无不相通”并非只是技艺上的一多或小大,而在于其是否为“成德”之人,即不是在一能和多能上进行区分,而是在技艺和德性上进行区分。有德之人虽然未必在技艺上无所不能,但是其德性在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在各种器用中得到表现,所以也是“无所不周”。
统观以上两种诠释倾向,第一种在于以技艺、知识之多少论君子人格,混淆了“器大”和“不器”的区别。第二种倾向则突出了孔子教育思想中注 重德性教化的一面,强调君子应当有德。但是如 果强调德为本学为末,也容易忽视孔子对于技艺学习的肯定、忽视技艺、知识学习对德性教化的意 义和作用,而走向两者的对立。基于以上两种解 释的偏弊,要全面地揭示“君子不器”所表达的思 想内涵,需要进一步在《论语》的文本脉络中把握
孔子论“器”的语境,理解“器”的多重指向;并结合孔子的思想把握孔子对于“君子”的看法,重新辨析孔子对待知识和德性的辩证态度,由此突破“君子不器”的诠释难题。
(二)孔子论“器”
在《论语》中,孔子谈及“器”的次数不多,除“君子不器”章外共五处。孔子曾说:“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1]163即完成一件事情,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器”是工具的意思。孔子又说道:“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1]148在这里说的是君子用人,重有才能的人,“器”是器重的意思,或者说是“以……为器”。无论从动词还是名词看,在这里“器”还是指向一种利于发展、生产的工具或人,是被作为一种“实用性”的“器”。这表明,孔子认为,正如工匠要善于利用工具一样,君子要善于去器重有一定的技能、技术的人,在日常生活和政治治理中,都不能够轻视“器”的作用。
另外几处“器”皆用于形容人。一处是用于讲子贡:“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 曰:‘女器 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1]76朱熹解 “器”为有用之成材,“瑚琏”是一种贵重而华美的 器[1]76;《集解》称之为“宗庙器之贵者也”[4]293。为什么孔子会说子贡是瑚琏之器呢?许多人认为,孔子在夸奖子贡是宝贵的人才①,但是这一解释并不全面。孔子在谈论自己学生的不同时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123即子贡以能言善辩见长;而在《论语》中,孔子多处论及只擅言辞不是仁的表现,如“巧言令色,鲜矣仁!”[1]48“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 佞?御人 以 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 佞?’”[1]76可见,擅长言辞的子贡在孔子心中不如 以德行见长的颜渊等人。而当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说:“赐也,非尔所及也。”[1]78也就是,孔子认为子贡尚未 能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在孔子看来,子贡是一个能言善辩,才智出众的人,可为社稷所用,因此评价子贡是“瑚琏之器”,肯定了子贡的才能,认为子贡是社稷之才;而朱子集注曰:“然则子贡虽未至于不器,其亦器之贵者与。”[1]76切中了此处的深意,这也说明子贡仍然未能“不器”,成为一个真正有仁德的君子。就这一处而言,孔子以“器”讲子贡,肯定了子贡是有用之才,
但也指出子贡尚未成为“不器”的君子,即仍不俱全德性,此处的“器”实际上具有了实用性和象征性的双重意义② 。
孔子另一处是用“器”讲管仲:“子曰:‘管仲之器小哉!’”[1]67朱熹注曰:“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1]67孔子进而指责管仲奢侈不知礼,可见其器量之小。程子曰:“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也。”[1]76可见,说管仲“器”小,是指其眼界狭隘、胸怀狭窄,不知礼节,不可正身修德。此处“器”由盛物多少的器皿引申为人的器量、气度大小,即已经从一种具体的使用转变为与人格、品质相关的用法,孔子借器喻德,这是在象征性 的意义上使用“器”。孔子肯定管仲的功劳,但是他显然不认为管仲是一个有德的君子。
孔子以“器”形容子贡和管仲,指出二者都未 能成为君子。孔子以特定的礼器指子贡,看似是对子贡的肯定,实际上是认为子贡虽然能言善辩,但是尚未成为一个具有德性之人;说管仲器小,则在指责其眼界心胸的狭隘。两处的“器”都内在与德性关联,无论是“瑚琏之器”还是“器小”,其 实都是因为其尚未能够树立完整的德性,因此要么是有技艺的“工具”,要么是器量小的“小人”。而孔子所认为的君子,不是只有技艺的工具,同时也要有大的器量,心胸宽广。在这个意义上前者的“不器”就和后者的“大器”统合起来,并共同指 向君子人格的建立。在这里,孔子借器论人,是意 图鼓励弟子通过自我修养成为有德的君子。[9]48
在孔子论及“器”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不器”和“器”的区别,还是“器量”之小大的区别,都指向了是否具备“德性”的问题,“器”具有超出实用性的象征性意义,与德性教化和人格培养相关。但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也并未否定作为工具性、实用性的“器”的作用,即其并不否定技艺的重要性。君子的关键在于其是不是“仅仅是器”,而不在于其“是不是器”,也就是,孔子并非主张君子不需要技艺、器能,君子的“不器”也要以“器”为基础,而关键是在于人是否可以“由器而不器”,既有技艺知识而又不仅成为工具,而是培养出德性,成为真的君子;管仲因为器量之小已然无德,子贡亦仍未能超越技艺而成就德性,因此没有成为真正的君子。
综上所述,就“器”的象征性意义而言,“不器”和“大器”都内在地与德性的建立关联,“君子不器”关注的,是君子在技能、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能不能进一步成就自身的德性,成为有德的人。这一点与孔子对君子人格的期待是相吻合的。孔子所追求的人格境界就是成为一个有德的君子,其教育的目的,也是在于让弟子都培养出德性人格。在《论语》中,孔子多处论及了君子的德行,都体现了他对君子人格的一种理想期待。因此,本文认为,对“君子不器”一章的诠释,应该把重点放在孔子对德性教化的重视上。
二、孔子教育思想中知识和德性的关系
上文已经从文本的具体分析中得出,“君子不器”所寄寓的应该是孔子注重德性教化的思想。但孔子也并不否认学习技艺和知识的必要性,这也使得“君子不器”这一章有较大的诠释空间。本节试图通过《论语》中孔子的相关阐述去全面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孔子看待知识和德性关系的辩证性态度,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在孔子的整体思想脉络中把握“君子不器”所表达的内涵。本部分旨在说明:孔子论“君子不器”强调的是德性建立的重要性,但孔子并不因此反对技艺和专业知识教育;有德的君子可以有多能或一能,只是德性培养不仅囿于技能的学习。
(一)技艺与知识
首先,当“器”作为一种实用性的“器”,指向 人的技艺、专业知识时,孔子是不反对这一类 “器”的,并且也主张需要技术教育或者智识教育。《论语》中有一章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1]94“艺”一般认为是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能,在孔子看来,掌握这些技能是有好 处的。而他自己实际上也擅长于多种技艺,《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 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10]3730他不仅谙熟礼乐文化,也能文能武,会料量、畜牧 等等。而“子云:‘吾不试,故艺。’”[1]110六艺的学 习看似是学习纯粹的技能,但在孔子看来,从事这 些活动的过程中也仍然可以获得德性的教化。以射艺为例,孔子认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1]63在射艺上的争,是君子之争,合乎礼仪,在射箭活动中贯穿 的是一个修德的过程。[11]64-66孔子教导学生的内
—18—
容,还包含“四科”“ 四教”“六经”等。四科即是 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论语》记弟子之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99四科中的“文学”和四教的“文”则是“六经”。孔子教六经,也是希 望通过经典阅读而传递经典中承载的圣人之道,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礼乐、道德精神,在为学生提 供智性知识的基础上,其教导的最终目的,仍然指 向学生德性的树立。
孔子虽然主张人要博学,教导弟子六经乃至于六艺,主张“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91。却 也并非主张什么都要教,什么都要学,也不认为君子一定要多才多艺。对于君子而言,技艺的多少并不是关键,只有一种技能或拥有多种技能都并不直接与其是否是君子相关。而看上述孔子教育弟子的内容,在技艺和知识之外,孔子更加注重的是诸如德行、忠、信等关涉到德性的教育,“游于 艺”更是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为前提的。所以,即便是教授技艺和知识,最终也服务于培养德性的需要。
在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尽管孔子认为君子并不直接与技艺多少相关,但孔子并不反对技艺和知识教育,孔子自己也是拥有多能的人。一方面,拥有技艺的人,即使他最终不能成为君子,也可以成为为君子所用之“器”,从而发挥其才能,做出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学习技艺和知识,具备一定的实用性技能或经史知识,是成就德性的基础。技艺可以为德性教育提供具体的现实场所,个体正是在具体实践的行为举止等方面塑造自身内在的德性;而六经等知识学习则提供了“斯文在兹”的文明视野,它们皆可服务于德性教化的需要。
关于孔子是否主张君子要多才多艺这个问题,往往还会引用到《论语·子罕》中的一段话:“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1]110对这句话历代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孔子看来,君子不应该有那么多技能[4]583;另一种则是孔子认为君子从不担心技多压身[12]172。结合孔子教育思想来看,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在孔子看来,多才多艺对于成为君子而言不是必要条件,但是也并非与此不相容。换句话说,君子当然可以是多才多艺的,但是多才多艺而没有德性,仍不能称为君子;只有一能,而有德性,也能是君子。因此,如果把“君子不器”指涉 的“器”和“不器”简单地视为是“一能”和“多能”的区别,认为孔子主张成为君子只能依靠培养“通才”的教育,君子即是拥有多种才能的人,显 然是不恰当的。
(二)德性教化
上文已经指出,尽管孔子不反对技艺、知识教育,但是在孔子的理想中,它们最终服务于德性教育的需要,是德性内涵的承载,或者说是德性教化在具体的日常实践和学习中的具体场域。在孔子看来,要成为一个君子,必要条件是成为一个有德之人。也就是说,只有技艺、知识却没有涵养出自身德性的人,无论其技艺多么高超,又或通晓多少技艺,都不是君子;而有德性的人,即便他的技艺和所知可能不是最高超的、最多的,也仍然可以成为君子。《论语·宪问》记载: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1]149
虽然羿、奡和禹、后稷都拥有某方面的技能,但是却得到了不同的结局,这是因为他们在德性上的不同,“力不足恃而惟德为可贵”[6]332而南宫适领悟到了这一点,因此孔子称赞他是君子、是尚德的人。而在《论语·子路》篇里面: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 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 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142
孔子不愿教学生这些技能,而认为学生应当学习的是礼、义、信。孔子斥责樊迟为小人,不是因为对这些技艺抱有偏见、认为君子不能学它,而是认为圃稼之事与君子的定位不符,樊迟要成为君子,应该追求的是自身德性的修养,而不仅仅是这些技能。
在孔子看来,只有技艺、知识而没有德性的人尚且不能成为君子。但德性作为抽象的品格,又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之中被呈现,所以朱熹注“君子不器”说:“成德之士,体无不具,用无不周。”指的是德性在实际践履中的通达。有关于德性的知识,不等于是真正拥有德性,它们是外在于主体的“对象性”知识,或作为客观的道德规范存在,拥
有这些知识还不等于主体真正拥有德性。德性的建立本质上是一个由外而内最终又通达于外的过程;即在学习对象性知识、在技艺践行的基础上逐渐培养出自身内在的德性,德性最终又依靠具体的实践去呈现。所以孔子强调行的重要性,君子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57“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74这意味着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践行。学习诸如《诗》《书》《礼》等六经也不是单纯为了获得知识的丰富,而是在于通过“诗”的学习去熏陶一个人的道德情感,把“礼”的规范落实到外在行为之中,并把“乐”的德性内化于人,实现德性的内外统合。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104-105“仁者安仁,知者利仁”[1]69。“知”应当有道德指向,否则知就会沦为纯粹的工具理性。一个君子最终呈现出的是非常整全的、通达内外的德性人格气象。
可见,孔子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外部学习而完成德性的内化和道德践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拥有真正的德性,而且通过自主实践得到自身德性的确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在现实践履 中 去应用所 学 的关 于德性 的 知识(knowledgeaboutvirtue)③,才真正意味着这些知识不仅仅是作为对象化的客体存在,而是成为与主体内在统一的知识,成为了“我”的知识,也就是成为了一种指向内在德性人格建立和道德自觉实践的作为德性知识(knowledgeasvirtue)。在这个基础上,君子能够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要求,最终便可以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此时这些知识早就内化为君子自身的德性,因此只要自然而然地行为,就已经是合乎规范的行为了。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德性如何可教?知识和技艺或许是可以通过直接的教育传递的,当代大学的专业化教育就可以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可是如果孔子主张教育目的是德性,那么德性如何可教就成为问题④ 。在这里,孔子的方式一方面是如上文所言,强调学生要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去领悟其中包含的德性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传承圣人之道,承载道德精神的经典阅读和学习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则是在技艺学习的具体实际场域中逐渐地去修养自己的德性。另一方面则在于君子的言传身教,也就是以自身的君子人格,发挥君子的典范作用,从而影响别人⑤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其实是“有意识地教其所知,无意识地教其所是”,通过自身日常言行的熏陶,在与弟子日常的对话、教导的过程中,教师的整全形象得以呈现在弟子面前,自然地以自身德性影响、教化弟子。
所以,孔子主张的“君子不器”就指向了德性的培育,有德的君子方能不限于“器用”本身,不是一个仅仅拥有外部技艺和表面知识的工具人,而在内部德性修养上能完成君子人格的建立,进而在外部的实践中践行道德而“用无不周”。可见,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人格的培养是重于学习知识技艺本身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是不外于人存在的,或者说学是服务于“成人”这一目的的。
(三)“不器之器”与“由器而不器”
孔子讲“君子不器”不在于否定技艺的重要性,而旨在强调要成为君子,不能仅仅囿于技艺方面,限于这一外部化的人格塑造,甚至成为被技术异化的“工具”;而要以技艺的学习服务于德性培养的需要,以成德之道去统摄器用。从“器”的实用性角度来看,君子可以为“器”;君子也需要一定的技艺和知识,否则难以安身立命;而如果从“器”作为一种与人格的价值相关的象征性意义看,说一个人为“器”即象征着人的工具化,君子则应该“不器”,即君子不应该成为某种工具,而应以自身为目的,从内部确立自身人格。如果从器的两个维度来看,君子可以说是“不器之器”,君子固然是“有用”的,但是君子却不是“工具”。
也可以说,孔子追求的是“由器而不器”,君子不是不需要技艺,而是有一定的技艺、器用,但是又不局限于单一的器用。何益鑫就指出:“故《礼记·学记》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不是说‘大德’不能‘官’,而是不以‘官’限制了‘大德’;不是说‘大道’不能‘器’,而是不以‘器’限制了‘大道’。”[11]68这里也一样,如果脱离实用性的“器”而抽象的“不器”,可能连“器”也算不上,比如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关于礼仪、纲常的知识或者基本的生活技能都不具备,则他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人,更难以说是一个有德的君子。但一个君子,在技术知识的学习中,也能不囿于外在的技艺,走向自身内在德性的建立,而能由“器”而“不器”,即由艺达德。
由此专业化教育和通识化教育,专才和通才的矛盾问题就被消解了,我们可以说,“君子不器”所指向的,本不是“专才”或者“通才”或“一能”与“多能”的问题。孔子不是认为专才或者专业化教育是不好的,而是强调,我们不能成为一个—20—
“没有灵魂的专家”[13]118,不能够只有专业技术的学习而忽视德性人格的修养。君子诚然当有知识和技能,但君子更要能够从内部建立起自身的德性,在实践中践履德性而实现德性的通达,因此,君子拥有的是超越于器物层面的胸怀和气象。基于这一点,“君子不器”对我们反思当代的教育是有深刻意义的。
三、结语
可以看到,“君子不器”所反映的孔子教育思 想,不仅仅关注于知识、技艺的教导,更重要的是 如何培养有德性的人。这样的教育,除了依靠教导以外,还需要言传身教,发挥君子的典范作用。孔子所注重的根本上是“人”的培养,在这个意义 上,是“人为主而学为从”。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中国的古典教育是有着深远影响的。在传统中国的教育中,德性教育一直是教育的首要目的,而知识性的、技艺性的教育则是次要的。中国以德性人格培养为目的的儒家教育传统与西方注重知识的教育传统有很大的区别,其以德性为目的而非以知识为目的。中国传统教育注重的是“知道如何”( knowinghow), 即如何实践的力行知识,“知识”本身在一种道德、实践的范围中被谈论;而西方教育则更注重“知道如是”( knowingthat),以求得确证的“真理”为教育的目的。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进入现代化的浪潮,工具理性价值的高扬和追求效率的社会模式,使得西方世界对于具体知识、技能的追求更盛,古典德性教育的传统逐渐失落。
20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增加,社会分工模式形成,对人的专业才能的需求增高。由此现代教育形成了严格的学术分科体系,学科划分不断向专业化发展。近代的中国也受到这一西方浪潮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都开始呼吁教育的改革,进行学科分科和专业化的调整。在古今—中西的交汇中,现代中国的教育也呈现出与西方教育一样的优点和困局。
现代教育模式固然具有许多优点,比如能够针对性地培养专业化人才,分工明确、让教育更有“效率”等。但同时也具有许多的缺点,日益细密的专业分工极具压迫性,大大地限制了人的视野和努力;把“人”作为“工具”培养,使得人依附于学,学问本身成为“外在于人的存在”,反而是“学为主而人从之”[14]39。
如罗志田指出:“太注重具 体,也可能导致人在学术中的隐去。由于‘学问上的分工愈细’,已到‘几乎难以综合的地步’。故‘学与学间,分疆分道’;而治学之人也只能以‘不同的方法,各走各路’,而‘成为各种学问之专 家’。且‘因每一人只附属于每一学,而又是附着 于每一学之分枝小节上’,于是‘从事于学的人则奔驰日远,隔别日疏,甚至人与人不相知’。以致‘除却其所学,乃不见其人之存在’,终因‘为了学 而失却了人’。”[14]39此外,现代教育也容易走向论才不论德的另一种极端,每个人都追求专业技术的拔高,但是却不再在意自身人格的培养,“有才无德”的人比比皆是,“高智商罪犯”频频出现。这是现代教育模式所产生的显著问题。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技术知识代替了德性知识,理性的霸权也带来了技术、专业化知识的霸权。
专业化教育固然有其优势,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教育模式下学科划分愈趋专业化的这一走向,确实使得“学”容易遮蔽“人”,从而导致人容易落入“器”的窠臼,忽视了德性的培养;也使得当代教育出现了价值危机。孔子的“君子不器”启发我们:人确实需要技术、知识,却不应当成为一个被外部技术知识异化的工具,要“由器而不器”,从内部建立起自己的德性,而不成为技术知识的附庸。从技术知识和德性的双重面向看,“器”与“不器”并不是对立的,君子有德,又能够在技术生活中不遗忘作为道德存在的整体生活。君子可以是“不器之器”,其实现的是内外统合下君子人格的建立,这一教育,旨在让人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因此,重新回溯孔子教育思想的德性旨归、辨明知识与德性的关系,根本意义就是为当代教育的个体发展寻求新的价值根基,以敞开个体生命的价值空间与价值本源,把民族精神和古典血脉带入当下,使得每一个个体真正地成为一个“整全的人”。
注释:
①如钱穆就认为,此章指子贡为有用之成材,瑚琏华美贵重,如后世言廊庙之材,并指出理解此处仅就本文,不应当牵引他说,因此理解本章不需要牵引“君子不器”章。但是钱穆并没有给出充足理由证明此两章是没有联系的。参见钱穆《论语新解》,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 111页。
②陈少明指出:“所谓实用性的器,就是孔子所说的‘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之器,即发展生产、方便生活的工具或用具...... 象征性的器,指用以代表其他观念的器物,器物与其所代表的观念的关系,主要不是基于器的物理作用,而是联想性的。”本文借助这一“象征性的器”旨在说明代表了德性观念的器,在这里器与其代表的德性的关系是联想性的。参见陈少明《说器》,《哲学研究》,2005年第 7期。
③黄勇区分了作为美德的知识( knowledgeasvirtue) 与关于美德的知识( knowledgeaboutvirtue),他指出:“在孔子看来,作为美德的知识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和它的来源有关。关于美德的知识或一般的理智知识只依赖智力( mind),而作为美德的知识还依赖心( heart ); 它需要一个人‘默而识之’(《论语·述而》),即在知的过程中获得属己的内在体验。第二个特点与其功效有关。它不仅仅是对美德的一种冷静的理解。它还促使一个人行美德,成为有德之士。”参见黄勇,崔雅琴《美德是否可教,如何教?》,《思想与文化》,2018年第 2期。
④比如,我们可以告诉一个人应该有关于什么的德性,如“你应该 爱你的父母”,他自然可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甚至可以把这作 为一个条文背诵下来,这是一种知性理解,是关于美德的知识。但是你如何能够使得一个人真正地拥有爱父母的德性?德性知识的获得意味着主体内部德性的建立,即需要主体把对象性 知识转化为主体自身的知识,并通过行为的方式去证明其已经 成为一种主体的知识。所以,如何通过外部教学使得他人拥有 德性就成为问题。
⑤《论语》中有多处都论述了孔子认为君子作为典范对他人德性应当发挥影响作用,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